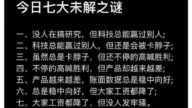一
這成都開往廣州的特快列車車廂過道永是那麼擁擠,那些不斷有往來幾乎是用腳在人和貨物間的小空際亂插著挨近廁所間的人們中間似總混入不停游避神情狐疑的「搭飛車」者;坐短途的農人總擔提扛背著不少雜物流動尋找可臨時堆放家什小憩一陣不拘什麼地處可否久待的空位;更不少賊似地提防列車員和乘警兜售粗製濫作臟臭害不知又花裡胡哨的小吃、多劣質冒牌帕襪衫攴巾紙指甲鉗之類隨身用品的小販,一併都普遍被認為礙事又障眼不予人愉悅又摒攘不去甚如賴皮的;小販們都練就了從容將裝滿貨品的挎包提袋甚至盛鹵豬蹄髈豆豉腐乾腊味腿肉雞鴨翅爪或酸咸辣味特重的腌制蘿蔔片絲怪味小點等的鍋盆籃簍即處快速塞到客座下即走開,輕捷得象僅僅是自然舒展下睏倦的身子骨稍事活動,警員才走又變戲法般一下恢複原神態自若逗覽游售端擎姿勢,諸多花絮竟皆恍若僅一時錯覺,均儼未實曾發生過一般。自更有量體訂製幾與過道一樣寬齊胸高推車、陳貨足夠多而無論前面如何壅堵也必自動閃避如航船破浪了無阻擾之憂;雖實成色均「好不到哪去」猶到處無呼亦應數錢遞貨無須多講喻天然而然,馭之者得慢條斯理矜傲扶行,儼維一統中心「主打」正貨無容置辯。
廂內照例充斥著混合了各色飲食品、類風濕病外用或防腐御暈之類藥品、脂香口氣、屁臭汗臭摻合坐墊靠背布套抑不知名什物發散的永遠說不上來的怪味加各種不爽人聲令人不得不眼神滯痴鬱悶沮喪;一應景象如同原始民謠古調加以時而清晰時而混沌的車輪軌際硬觸聲之單一乏味,直宜催人昏昏欲睡。
不時有列車員乘警帶「部隊化」的異韻硬性語氣招呼架上行李須碼放規範不得外冒坐姿必端正不可有礙觀瞻阻通行等,且定時疊換著實令人提神警醒。
車內車外浮影晃蕩,予人恍然進入「時空遂道」之感
二
靠過道位上是一著淺藍有領短丁恤瘦削而白晰的中年婦女,燙過的花白頭髮略捲曲,在兩頰之上用大別針高高別向腦後,額上有稀疏的內彎留海,高鼻樑,黑瞳眼光迥迥有神,似有使不完的精力,好打聽事由卻惑于無的發端而微陷悶悶不樂。挨她坐的一戴眼鏡微發福女孩,許是己步入社會好幾年的青年會計師,延途總不斷與她靠窗坐的偏老年父母熱乎不無炫誇地講述他們在海南購置的新居及附有優越的環境,另還有些親戚也在同處購房,每年得同隨季換居之愜意;而此行大概去往正是那裡;不錯的生活,正象他們沿途展露檯面頗受用完備又精美的葯膳飲食品,這讓他們格外有面子。中年婦于簡單打招呼外便覺缺少摻合進去的機會,雖屢屢意欲表明自己和他們屬同一圈子擁景況近似的生活,亦頗多感觸神往。和她正對坐中年男乘客大概更樂於到另處與熟悉的伴廝擠,其空位多半時被過道另側的互換著臨時享占無話。那當中是位老將灰布褲腿亂皺皺捲起露出粗而顯腫脹發亮的絳紅色小腿又不停打盹的中年村婦,這情景自使她有些掃興,何況村婦常乾脆倚一肘斜趴窗前小台上引得緊挨的車窗邊老男客及對過的老伴不時微皺眉用一種打量冒撞的狗的神情打量她,他們女兒也不便說啥,自顯得不大高興,尤其是她還時不時肆意扭動板硬的身軀,彷彿有些不地道,那簡直有些挑釁的意味,若不是她總埋著頭疑有惹嘴角之虞;中年婦顯然也覺不便問村婦話,懈了興緻而暗蓄蒼勁。不過她仍于村婦在一沉沉長睡後淚眼始干神志呆愣當口帶著居高臨下氣勢逼人的口吻看著她發問了:「嗨,你咋搞象接連兩天多沒見吃喝光睡,受得了啊,你啥地方的,幹啥的?」是大咧咧北方口音。村婦遲疑了好一陣,彷彿內臟神經醒得更晚,末了終感對方盤問時顯然的戾氣,那象是常遇到不得不快快如實道來的,於是她用帶本地鄉村的方言下意識促促回應:「我是溫江來哩,我到廣州找我老公。」「廣州」聽去成「瓜州」,象雜物包傾倒外流聽去不順暢須重溫語意才能明了。「那有孩子嗎,誰帶著呢?」「有一個女兒哩———–不過剛走不久,才半月前。」「什麼,你是說剛離世不久?」她失神默默點著頭,眼光迷朦象又要昏昏入睡。「是跳水死哩——–天下黑嘍鎮派出所哩告知家裡下午有人在江邊看見水中漂動的女孩頭髮和花衣服報了警打撈上來哩。」她更快地說,聲音發嗄,竟如偶然逢遇宜釋懷去處一種了結,又滿帶預想中多會失望的模糊惶惑之壓抑,那有些上窄下寬的絳紅臉瞬即緊繃,眼睜得老大,顯見得胸脯起伏加劇了,一如粗心犯錯的蠻姑包不住孽情俟挨毋明的遭罰。「為啥會哩,是為啥哩?」中年婦聲音柔緩下來,態度也和藹許多,「你女兒多大,長得啥樣,胖不胖?」「已經拾參歲嘍,不胖,和你一樣瘦個子,趕她爸爸,他瘦——–」言及此她聲音顫抖了,眼眉現出明顯的恐慌,「我———-」接著她欲言又止。中年婦見狀,倏諳當必遇事不明底裡見識短淺之人罷,務宜循循善誘導引她自行闡發饒得從容聽故事只需于不甚明白處略一岔問,自亦必心凈無恙的,於是恢復了先前平和從容靜待其自述。
象多數「腦筋不夠用」的人一樣,村婦似礙難於不知從哪說起,未免結結巴巴語無倫次,又所言恰當中聽與否會否常錯之迷惘,確非自己慣能面對承受故恐懼有加,眼前說呢不是不說又不行儼情勢所逼奈趟獨木橋,故說一段又語梗眨巴眼看她似望祈獲難予確定的首肯而後方能接敘,終於說解錯雜續續停停中道出經歷大抵梗概。
三
「———–她原來最聽話的,又曉得幫著做事,後來說是聽其他班上同學暗中說了他們班幾個長得好的女同學都讓老師安排由老師帶出去開房尋歡事,還說是幫了老師大忙,老師升遷了定讓她們都有光明的前途;她們都得了錢,天天買東西吃又游公園坐轉轉車,但說回家這事不準告訴家長也不許外面講一個字,否則不幫她們還要被開除。天———是哪樣野獸嘛,干這樣事,對這樣小女娃作孽心能安寧不是!想來老師咋會嘛,講給誰誰信?我告訴她這些聽不得,是壞人編造出來起壞害人的,沒有的事;我們這樣人家只知道好好老實用功讀書將來努力工作才得過安穩日子,噢!別著一肚子氣說這種事本來實在說不出口的,害怕她中邪啊,她倒說我騙她,說她們早知道其他學校裡也這樣,據說好些得到漂亮小女生幫忙的領導官都升得快而且升大官,甚至有當上副市長的,也都給那些小女生安排了重點班名校;但也有成了痴獃或生了無法治愈的病,都不準講的,家裡人有冤自也只能喑了誰敢亂說不害死自己娃!還說到處都小道傳說現想爬官的全這樣,搞這些小女娃搞得越多的官升得越快官越大,所以人人都拚命地在找機會幹;真有好多小女娃都想得到他們喜歡而不曉得自造孽的哦!———-
「當然我急起來說她也說得緊,不准她想這事說這些都不是真的,後來她倒發急兩手亂打我又亂抓起東西砸我,那是在她說是在同學家電腦網羅上看到一位象她二姑媽一樣瘦弱又一樣文靜的阿姨之後。她二姑媽就不論有啥難事受冤枉被老公打傷講起來都是溫柔平和從不暴躁,不是象我們樣忍不住就會跳起來的,她偏就最得丫丫心服——她小名叫丫丫。那阿姨講到她丈夫在沒見出示任何合法手續的情況下不由分說被抓捕監禁又活活冤枉被長時間挨餓,毒打,不準睡覺、洗澡,受多種令人吃驚難以置信的酷刑,都是以前在小說裡才見,從老師講述舊社會罪惡時才聽到說的——而直致殘致死還不准她帶著他們四歲的獨生女兒探監看望,不準問詢了解實情和討說法,她們堅持合理要求還也挨暴打辱罵被關恐嚇,現遺留下她和還不懂事的女兒于極艱難絕望中謀生苦挨日月猶如被置於漂泊人世大海上遭臨狂風暴雨孤立無援的人生小舟岌岌不保——而她講述驚心動魄遭難經過時竟沒有一句怨恨的粗話沒有狂怒痛罵,態度溫和平靜甚至寬厚得象僅是不幸遭遇一群完全無家教不懂事無人打理的野孩子肆虐,儘管眼裡飽噙浸漬無盡冤屈磨難的淚花;四歲女兒嬌弱稚嫩的小臉呈現出多麼不對稱的成熟凝重表情,臉蛋兒上掛著本屬天真撒嬌的晶瑩淚珠竟滿聚人類深重災難縮影———–自那以後丫丫變得更孤僻怪異。連對我她也不願意多說話了,寧願時常和鄰家捲毛小狗親近;你說家裡也不容易吧,有點好的也捨不得吃留給她,她都要先拿給捲毛小狗;後來一天下午放學回來聽說小狗狗被汽車壓死了,她不顧一切跑去跪下抱著它失聲痛哭,又將自己最好的那件花衣服給它蓋上象在哄更小的小孩睡覺,埋下頭緊貼它哼哼哼地哭得痛徹心肝再不肯離開。看見她那樣我更是難過得胸發痛,也自那以後胸梗痛就再沒有離開過我。
「我知道丫丫是乖的,我又不能過度怪她,我說不了她又沒辦法。」說到這兒她有些不能自制,兩眼發紅淚花轉。
「自那以後覺得受點氣就經常獨自發獃,說不聽而且一點也說不得她,一說她她就:『不聽不聽不聽不聽假的假的假的哪樣都是假的哪樣都是假的哪樣都是假的!———–』
「後來又渾亂說氣話:『原來你們也是和老師們一道 合起伙來騙我們的, 拿我們來隨便玩,玩夠就不要我們了, 等我們去難過一輩子, 然後就去死得很悲慘很難看,只選長得最漂亮的去幫著他們再騙!』 ———–末了似還怪罪將她生到世界上來全是我們錯,憤恨不已!那以後又時興動不動扭甩小身子胳膊皺眉促顏聲音顫慄地說:『為些哪樣嘛為些哪樣嘛為些哪樣嘛為些哪樣嘛?———-』象腦筋忽被過度壓抑受傷腦殘樣又好象變小回去了。」村婦說到這兒情不自禁學著憶想中她的小丫丫慣常的情態將笨拙乏姿的身軀臂膀也硬去扭甩,模樣看去不是味很招笑,她卻陡然破聲沙啞痛哭起來,即將放聲號啕大哭隨又忙將兩袖交替掩面屏氣強忍住似畏避自己哭相太不雅虞遭責難或提防已因明顯過度悲痛使自己已然傷了身的哭泣;顫巍巍的哭聲鎮定了,眼淚也已揩乾,但瞬即發紅的雙眼、起皺的眼角和似忽高聳的顴骨卻再無法撫平,新涌的淚也不斷糊住視線,現一副愁雲慘霧哭相,那象是業經生存煉歷烈火鍛燒,豈易得平息!
「你想,我除了這樣說能咋說嘛?」她為自己開脫說,仍用衣袖拭著眼淚,「她爸爸趕回來沒問我一句也沒看我一眼,象全該怪罪於我,辦完娃的後事即買車票走了,簡直根本不和我說話也不問老的情況。」
「你們家庭關係一向還好吧?」聽見問,她倒平靜下來。
「以前很好的。後來很長段時間沒給家來過電話,也很少問到丫丫和她婆婆;因婆婆患肺氣腫帶不了丫丫,我得留家裡照顧她婆孫。以後一次偶然中從鎮上和他一起出去打工的嘴裏聽到他在外面又———-」她又說不下去了,低下頭用手撫胸,象又要哭。
中年婦敏感地接茬道:「你現在找他,那他告訴你現在的地址了嗎?」
「沒有,我只有先找和他一起做事的去打聽。」她有氣無力回答。
過道另一側的年輕男女們似都早早留意到她的敘說,此刻也以靜默回應,彼此面面相覷。和她坐位對應居中的年輕瘦小夥子大概模仿電視名人秀節目用手作響指姿勢說了一句不明意義的「經典!」
沉默,一種醞孕異想的沉默。
須臾,靜聽了好一陣的老年男客輕緩地發言了:「別說了吧,要說,應撿些高興的事來說,旅途嘛!你看,弄得大家不高興,你自己也不好過,是不是?休息會兒!」聲音尖而沙啞,帶著長者的權威口氣,又補充說:「家醜不可外揚,對么。」
村婦扭頭這邊看時,見青年會計師映著亮亮的白邊眼鏡,橫眉冷眼面無表情,而那母親似乎無話好講,這當口兒四目相對即現出了親切圓滑面:「休息休息,你該是很餓了吧,來,吃點東西,嗯?」手指著小桌上的橙汁糕餅說,並沒動手拿。
「謝謝,我不餓。」村婦冷冷地回答,收回了眼光。她似早經熟悉這類客套,漸漸減除了原來那鋪天然的謙卑,內心已然習慣蓄積一番抵觸,衍生陣陣無名怒火:「說這種話,別人遭災受難你們看來居然覺得是泄丑漏穢,你們還真會有關心別人的時候?!倒好象別人自己這條命也須由你們認可才得活才該活是吧,老一套,呃?!」不由眼光裡透顯出一絲粗野來。似也正因這陣暗蓄的野性激情讓她那拙嘴笨舌漸變得順暢起來的,若非突被阻斷,那憤慨激情定不能自控,徑直要凶涌而出了。她本也對能否找到老公、能否挽回夫妻關係不抱太大希望,也不再有很強的心愿,現在象她這樣家庭處境實在太普遍了,暗已成為社會大趨勢,不過說不揭示不傳揚甚至盡量掩蓋罷了,人人似都心知肚明,故無可如何也不太在意的了。強佔強攤強拆遭辱毀家傷人致命之事隨時發生如家常便飯,多少人拋妻棄子豁出命去干也是常聞常見為社會所逼無足怪。這些似亦漸融入日常生活溶於血液透進骨髓,也在她靈肉間植入反抗的因子,生出盲動的興奮情志了;在她意想中大不了也隻身投入那未知後果如何的反抗大軍死而後已,也算踏實走過涉世之路了,彷彿她此去以其說主要找那個「他」不如說是去找那總給予她希望和力量而實連自己也本身不保的尚未謀面的「他們」,不過這已不緊要已不會再有何顧忌猶豫。
她緘口埋頭抱臂,不再去理會周圍人們的眼光意見和想法,似又準備權縮身心進入她的「時空遂道」 。
火車朦朧隆隆駛入昏暗的夜。
作者袁國祥
2013.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