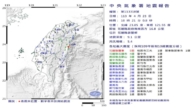【新唐人2006年12月12日】【人傑地靈】魏京生(5)堅持:國外大資本家跟共產黨合夥 非法剝削中國工人。
93年我被釋放的時候,有一天他們突然說放我。我說中國的刑事訴訟法裡的假釋是有條件的,因為刑事訴訟法上寫的非常清楚, 假釋的犯人必須首要條件就是認罪伏法。而我不認罪,我不伏法。或者說我不認罪我伏法,我遵守監規紀律了,但我不認罪。我說你能放我嗎?這是缺少要件啊!他們只好說,“上面要放你,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你不要跟我們繞法律條文什麼的,你趕快走,我們也好完成任務”。所以中國這個法律,他抓你不合法,他放你的時候也不合法。
當時出獄的時候還發生了一個很大的爭議,就是我想把這些年積攢的書信底稿帶出去。很多老員警很早就勸我,說按照他們的紀律,這是不可能的。我說我不管什麼監規紀律,按照法律,這是我的私人財產,沒有什麼理由不讓我帶走,法律也不能剝奪我的私人財產。可是他們仍然說不行,按照規矩不能帶走。我說那好,不能帶走我就不走了,於是我就解打好包的行李。他們一看急了,說等會兒,我們去請示司法部。我說那好,就給你一個小時去請示,不然我就要解行李了。他就去了,過了一個多小時他回來了,說能不能讓他看看那些信。我說你甭給我來這套,我所有的信都是通過你往上轉的, 你都看過,你甭跟我玩這花招。他猶豫了一會兒: 那這麼著,你帶走吧!我覺得這些書信很幸運 ,這些帶出來的信稿最後編成了一本書,能讓大家看到當時監獄裡的實際情況,包括我那時候做了些什麼事,大家都可以通過這本書看到。
93年我被釋放了以後,當時很轟動。人們都期望通過這麼一個釋放,透露出一個信號,就是中國的政治氣候可能會變得好一些,也許會走向民主化,總之人們是懷著這種希望吧。當時這個消息剛一傳出來,在我們家的大院子裡,站了滿滿一院子外國記者,公安局統計了一下可能有300多,最多的時候達到400,平常老是保持在300左右。那些外國記者,一直在那兒等了我一個星期。公安局的這些警察就帶著我四處躲藏。這也表明了它的虛弱之處。據說江澤民去請示了鄧小平,說為了奧運會,把這個人放了,鄧小平就批准了。但是江澤民還是很心虛,害怕這些外國記者,也就是說害怕輿論。事實上,中共的很多做法,哪怕是它做的件好事兒,它都擔心見不得人,也就是說他們是完全沒有自信的一種政治。居然讓那幫員警帶著我在外頭到處遊玩,當然都是公家的錢。遊玩了一個星期,一天換一個地方,就是躲這些外國記者.
十五年之后
我蹲了15年監獄之後,出來我看到的這個中國,巳經和15年以前完全不一樣了。道德的淪喪,當然現在更糟糕。但是93年就已經是道德淪喪,文化破敗,崇洋媚外。當然學點兒西方的東西也不一定是錯的,但是你自己文化傳統裡好的東西,包括從民間發展起來的很多東西,或者是東西方結合的一些文化的東西,都得不到擴展,反而是一種畸型的發展。詳細的情況我就不講了,當時很多情況讓人看了觸目驚心。我就覺得中國真的變化很大,這個變化並不是一個好的變化,而是一個壞的變化。但是確實在中國也仍然有一大批一大批的仁人智士。
那個時候都還沒有什麼工運,工會運動, 但是工人的情況已經變的非常糟糕了。過去在那種所謂”全民所有制”的那個時代, 工資不高,待遇又不好,但是畢竟還有穩定的待遇。但93年的時候失業狀況已經非常嚴重了,這也是讓我沒有想到的事情。我那些在全國總工會工作的朋友跟我講了一些情況,說在底下已經幾乎到了要造反的程度,沒有飯吃,沒有一點錢。現在全國總工會做的工作就是求爺爺告奶奶到處找救濟款,實際上等於是救火隊。總工會找一點什麼破衣服和一點兒糧食什麼的,拿去救濟工人,讓工人別造反,當然還是為了維護共產黨的統治。他告訴我他下礦區去視察的時候,發現那些下崗工人的狀況,就像我們在過去回憶舊社會的那個展覽會上看到的一樣,至於舊社會是否是那樣,我們都沒親眼看見不敢說。但是他說,“現在的工人就是那樣,就是說現在才是真正的舊社會”!他到一個老工人家看,那真是家徒四壁,坑上除了一床破被子,什麼都沒有,沒有糧食,沒有任何東西,家裡面所有的東西都賣光了。他說妳們這些民主派人士,不能天天在那光喊民主,得關心最基層這些老百姓的生活狀況,否則就要爆發巨大的動亂。他說89年是鄧小平說那是動亂,但那根本不是動亂,那時候社會秩序還挺穩定的。而現在93年,那真的是要社會動亂。那麼多的下崗工人,沒有人管他們的生活。當他自己下到礦區去時,工人領袖直接找到他,說我知道你是從中央來的,全國總公會來的,你就給捎個話,告訴中央:“要不,你現在給我弄來救濟糧,要不這工人就得造反了。我們就得拿起武器造反了,我們現在也能買武器也能造武器,這手藝我們有”。 經過89年那場運動後,大多數中國人都看清楚了咱們需要的是民主,民主挺好。就象北京的處租車司機說的,“至於民主是怎麼回事兒,我也弄不懂,我也不想弄懂,但我就知道一條兒,民主是好的,比現在好。”
我當時非常奇怪,我們79年的時候,就去幫助這些上訪的人,包括後來胡耀邦也弄出很多什麼上訪的制度,怎麼弄了半天到了93年還有那麼多上訪的?最近我看了很多新聞也說國內上訪的好像比79年的時候還要多了。所以應該說現在的社會矛盾,其實比79年那時的社會矛盾還要尖銳。而現在的這個矛盾已經不是老百姓滿意不滿意的問題了,而是一種非常尖銳的階級矛盾。一部分人把持權力的同時把持著財富,把持著所有的社會資源,而大部分人則喪失了這種權力和資源,而且得不到自己的利益,生活處於極端貧困的狀況。那麼這個社會的基本矛盾應該是當前中國社會最基本的矛盾,所以共產黨的那個政權不穩,可能跟這個有非常直接的關係。
第二次入獄
93年我在外頭當然也開始號召大家搞工人運動,包括要組織反對黨。當然我的這些活動,可以說是戳到了共產黨的痛處了。我並不大肆張揚,也不是天天去見外國記者炒作。他們一開始以為最大的威脅來自這些外國記者,但是我們做紮紮實實的工作,號召工人農民去維護自己的權利,這個讓共產黨發現也是不可容忍的,所以很快又把我抓了起來。
抓起來的過程也是一個小故事,是稍微有點傳奇性的小故事吧。當時在美國已經有一個很大的爭論了,就是要不要把人權和貿易脫勾。柯林頓政府為了拍中國政府的馬屁,滿足美國這些大資本家的需要,就要把貿易和人權脫勾,這是六四以後一直在給中國壓力的一個政策。但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產生了很大爭議,當時有好幾個議員到北京和我談到類似的事情,其中最嚴重的一次,就是當時的國務卿克�斯多福,他想到北京去聽我的意見,然後以我的意見為準,來解決美國這場爭論。所以他就決定來中國,讓當時讓助理國務卿沙塔克去打前戰,悄悄的在美國大使館那幾個朋友的幫助下,跟我們聯繫上了.
據說是第二天江澤民把公安局給臭罵了一頓,說人家見面都見完了,你們還不知道,你們該加以阻止,你們沒有阻止,所以就讓公安局把我給扣了。他們就跟我談判,說我們請求你不見,我們願意提供很多交換條件。他說了好幾條:
第一,你只要同意我的條件,你的人我們不抓.他把所有民運的人都算成我的人。我說巳經抓了的呢?他說,巳經抓了的很多人我們會放,我們現在給你一個十五人的名單,我們放這十五個人,其中包括王軍濤、陳子民等等人,其他很多不是那麼有名我們就不提了。這十五人名單,你看夠不夠,我說這不行,太少了。馬上他就拿出一個三十人的名單, 說這名單你看行不行。我說你說話算不算數,他說只要你現在同意我們的條件,不見克理斯多福,我們就放名單上的人 。他說我負責的跟你講,這是江澤民在跟你談判。我說還有這二天剛剛被抓的呢?誰誰誰誰誰,我點了周國強等幾個名字,他說我馬上放,明天就放。他說你不信你明天可以打電話。
第二,我們知道你想組織工會,在一定的程度上我們可以給你放行;你要辦報紙,准許,我給你找批文去,你幫助丁子林這些人,以後我們不幹擾,放行;你們轉款我們一律不扣。
然後他問我還有什麼要提的條件。我發現他們真的很瞭解我,我要能提的條件也就是這些了。
我知道共產黨是不講信用的,但是在那種情況下他提出來了,你要不要冒個險。如果真能有這麼一個機會,通過談判把這個做成了,當然是件好事。哪怕共產黨不講信用,我覺得我可能也要冒一次險,頂多最後被別人罵成是傻帽,受了共產黨一次騙。說實話我很對不起克理斯多福,因為他去見我也是冒了很大的風險,中國政府對他的壓力也非常大.
當時談得很清楚,他們要求我的就是,在克�斯多福在中國期間不要回到北京。我當時還追問一句,那麼在克理斯多福離開中國之後,我是不是就可以回北京了?他說當然。所以我在外頭轉了一圈兒,當然是在警察的監護下啊!我到青島看了幾個親戚,到濟南去看了幾個藝術家。
當我到濟南的時候,克理斯多福已經離開中國了,所以我就跟他們說,克理斯多福已經走了,按照咱們原來的談判條件,現在我得回北京了。這個時候他們就反悔了。陪我的人說老魏呀,咱們再玩一玩兒,到南方去玩不是挺好的嘛,南方你還沒去看過,這改革開放…說了一大堆。我說你不要跟我說這些,我可能會去南方,到那個時候,你們可能就沒興趣陪我了。但是我堅持說要回北京,我就讓我的司機開車。中途到天津停了一下,只見了一個朋友,因為這個朋友有很強的官方背景,他父親是原天津市公安局局長,所以我覺得他可能不會受牽連。後來我才知道,我一離開他們家,連他媽都被公安局抓起來了,共產黨這方面是絕對沒有人情味的。但我見了這個朋友,聊了聊天,這個朋友也警告我,說我很危險, 說壓力很大,他們也聽到一些消息等等。還告訴我要小心。
在天津停留期間,我順便考察了一下天津保稅區。他們講了很多實話,他們說,所謂的改革開放、所謂的保稅區,其實就是把外國企業放進來,偷稅、漏稅。外企在中國用了便宜勞動力生產了東西以後,價錢算得很精,進來的原料很貴,出去的產品比正常市場便宜得多,這樣他給你算好了,正好中間沒有利潤,所以他就不用向中國繳稅, 當然他們還用了中國便宜的勞動力。我問那還維持這保稅區幹什麼?他們告訴我,至少有一個好處就是安排了一些工人就業。雖然工資很低,特別是台灣人和韓國人開的廠子,工資很低,日本人開的廠子工資也不高。我一下就明白了為什麼國外的很多報紙會對中國的報導那麼的正面? 是那些大資本家在報紙後面,在跟共產黨合夥的、非法的剝削中國工人,剝削的錢把自己養肥了以後,在外面替共產黨說話。當時我就是這種感覺,不是我到美國後才瞭解的情況。我當時的直覺就告訴我,這就是江澤民搞的一套外交,就是利用這些外資企業來控制西方的輿論、控制西方的政治,這個他做的很成功,就是在中共的邪惡的手段上又加了一個手段,這是江澤民的功勞。
我到天津的時候,矛盾已經很尖銳了,跟著我的這些警察拚命的阻止我回北京。我問你們當初答應的條件不算數了?他們的回答是:不算數了。於是我被扣押了。前幾天是一種臨時性的扣壓,然後就轉為長期性的扣壓。
釋放
總而言之,不管怎麼樣,在我第二次入獄後還發生了一些有意思的故事。大概是95年,隨著柯林頓做了讓步,中共的國際社會壓力一下子減輕了許多;所以96年下半年的時候,中共召開了一個什麼政法會議,羅幹主持的,當然是江澤民授意的。意思就是現在我們國際社會壓力已經減輕了,我們現在終於有機會來收拾一下這幫政治犯了,我們要採取嚴厲措施、整肅監獄。
那麼這些措施出來以後,全國的政治犯都受到了迫害。當時我聽說了消息以後,我所在的監獄也開始出現一些奇怪的現象。他們經常悄悄地召集那些看我的犯人去開會,開完會以後,其中的五個人都不願意動手,只有一個,那個小組長,他願意動手。所以這個小組長就不斷的找我麻煩,無緣無故的找我打架。我已經覺察這裡有點奇怪了,因此就在思考怎麼對付他們。因為正好快96年的年底了,我就想,97年江澤民有個大秀,他會非常高興的一個大秀。鄧小平爭取了多少年,終於香港在97年7月份要回歸了。江澤民會很得意地的做一場大秀,這都是咱們能想像的。
然後我就算計著,我如果把這個消息傳出去,就是他們在監獄裡歐打政治犯的消息,肯定會很轟動。那麼我就根據這些我所知道的情況,我就進行設計,哪怕他揪著我的胸口來挑舋,我也不動手。我不動手,但我等,我一直等到97年的四月份,他再伸手挑臖的時候,我就不客氣的把他教訓了一頓。一動手果然跟我預料的一樣,馬上警察就來說,這是你的問題,你打人家,我們要採取這樣這樣這樣的處罰措施,包括上銬什麼的。兩個星期以後,就在每個月接見的時候,我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我弟弟,然後他再告訴我在國外的妹妹,然後國外的妹妹馬上通知劉清, 劉清就去炒作。所以後來江澤民得意洋洋去接收香港的時候,從查爾斯王子和安南開始,每一個人見他都要問到這件事,聽說你們現在在虐待政治犯? 江澤民回答說沒有。沒有?那最近我們聽說魏京生怎麼麼怎麼樣,你要說沒有,能不能讓我們去監獄視察? 弄得江澤民很尷尬,回來以後暴跳如雷把這個羅幹給臭罵了一頓、把監獄裡對待政治犯的措施全部取消。
出國
很多人會很奇怪,為什麼我堅持在國內那麼多年,眼看就要得諾貝爾和平獎了,為什麼要出來? 但是我得解釋我出來的原因。得獎當然是一件很好的事,可能對中國的民主運動是一個很大的鼓勵、對中國老百姓的民心是很大的鼓勵,但我個人並不很看重這件事,而且我覺得,這種鼓勵雖然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我堅持那麼多年不出來,但是最後在97年江澤民跟柯林頓做了交易之後,他們來跟我談的時候,我思考了半天以後我決定,還是要出來的。
第一,我確實身體很差,警察們也都好心的提醒我,再在監獄裡待下去,可能沒辦法活著熬完第二個星期了。那麼我是死在裡頭, 對民主運動的幫助更大?還是出來幫助更大呢?當然,出來可能幫助更大,我不必要死在裡面。第二,更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我當年覺得海外的民運吵成一鍋粥,這個是我在中國的報紙上都能看到的,共產黨是不忌晦報導這些負面的消息的, 反而是加強報導。通過共產黨的這些報導,我發現海外民運一個很大的缺陷,就是他們的工作到了該轉型的時候沒有轉型,還是熱衷於在報紙上和街頭上炒作。
上述做法在89年剛過去的那二、三年裡頭,可能還是比較有效果的,因為那時候,大家還是比較關注中國的事務,包括那個屠殺,人們仍然記憶猶新。但是時間久了以後,人們的記憶就不猶新了,熱度也就下降了,這是很正常的。那麼海外的民主派的工作呢,應該有一個轉型,包括對國內的指導性的工作。
97年當然也是因為在政治壓力之下,當時江澤民要訪問美國,我估計江澤民來美國肯定是有條件的。你要說他賣國,他真的很賣國,而且是拿著中國人自己人去做人質跟人交換,這個在過去已經有很多例子了。 堅持
出獄後,在機場跟家裡人見了一面之後,我就被直接送上了飛機。我一到美國,有很多記者就問說,你在飛機上可能會想很多、好像感情會非常激動。我說我一點都沒有。因為我坐在飛機上,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到了美國會面臨特別特別艱苦的工作,哪有時間去激動啊!我一點都沒有激動,我真的是一點都沒有激動!
當然到了美國以後,我所面對的這個狀況也是很糟糕的。首先來講,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大家都來歡迎你。第二點,熱情支持民運的人非常多,但是呢我在這兒是任何人都不認識,又由於美國這種環境,我很難跟大家碰到一起。而當時,美國方面安排的一些接待的組織和人,也並不一定非常關心中國的民主,他們關心的當然是他們自己的那個形象。
所以這幾種情況加在一起,就是說我到美國以後剛開始工作,環境是錯蹤複雜的,也是非常困難的。所以這�我得給大家交待一下。大家對我們的期望很高,而我們並沒有達到這些期望,那麼這是有很多客觀原因的,確實不是我們自己所能左右的。當然以後隨著時間的推移,工作慢慢展開,我個人覺得我們在海外的工作還是不辜負父老鄉親的期望,還是相當有成果的。而且說實話,一個運動在沒有真正的外援的情況下,不像大家傳說的那樣,美國人給我們很多錢、台灣人給我們很多錢,並沒有這種情況。那麼主要是在靠大家自己掏腰包,艱苦奮鬥搞民運的情況下,還能做到現在這個水平,還能保持這個運動的存在,我覺得這已經是非常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