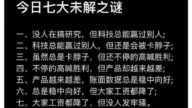【新唐人2012年3月31日訊】儘管我有車,但想出這個城市,不是說想走就能走的,去往城外的公路多是高速路,雨雪天或大霧天,說封閉就封閉了,如果硬要出城,可能蝸在郊外的所謂國道上,前面與後面是望不到邊的車流。
機票並不貴,但有時在機場,飛機就是不起飛,那邊說這邊空中管制,這邊說那邊天氣有問題,有時坐飛機,與坐火車花的時間沒多大區別。坐地鐵吧,票價便宜得讓任何其他城市的人眼紅,二元錢可以通行整個北京城,但東直門、西直門換乘,你一定會罵設計者腦殘,或者地下或者地上,按著他們劃的箭頭兜圈子,不讓你走上兩站地,他覺得便宜了你。
地鐵廣播還有義務宣傳員,總會提醒你,不要與陌生人說話,要自覺抵制別人的乞討行為。乞討者一般都是生活無著落的人或殘疾人朋友,給他們一元錢二元錢,完全是民間的一種小慈小善,為什麼要將人心弄得拔涼拔涼的呢?如果政府保障到位,誰會閒著沒事到地鐵裡乞討,除非在搞行為藝術。
當走出地鐵向人問路時,我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人們閃過我,對我問路一點表情都不給,就匆匆而過。人與人之間,總算是一點關係都沒有了。只有掏手機,打電話給熟人,指點迷津。如果沒有熟人,你就是城市漂流瓶。
開車在城市裡,北京大得嚇人,出門在外辦事,沒有半天時間找不上別人的門,找到門了,你卻發現找車位停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日新月異,以前覺得是一個美好的詞,現在變得異化了,任何一個居民都覺得自己在這座城市裡變成陌路人。
一些人在辦公室裡劃一個圈,一片老城就拆遷走了,再也找不見蹤影,不僅將老市民們的記憶給快速抹去,也使我們新移民失卻從容與懷舊的心情。發展二個字,成為城市的神靈,但有多少人分享了發展帶來的福祉與利益?發展是一位財神,只垂愛權貴,而不是太陽神,不能普照所有的人。
水漲價了,看著那麼多的人浪費水,我理解政府,想想北京缺水時,水從山西調配過來,從河北分流而來,甚至要從長江開渠引水而來。如果久旱無雨城市人將如何生活?加上流動人員,北京可能已逼近二千萬人之眾,斷路、斷電、缺水、雨雪之災等等,都可以給超大型城市以重創。但我們仍然熱衷於造大城,而不像二千年前柏拉圖所追求的那樣,造幸福之城。
硬著頭皮交愛國與環保的水費,我覺得沒什麼,但城市上空的陰霾卻總是揮之不去,罩在城市上空,加上汽車尾氣,地上塵埃,經常讓我呼吸覺得困難。今天晚報上專題介紹城市陰霾天氣,說是空氣無法形成流通,所有的廢氣停留在城市上空了,挑戰每一個人的身體健康。
回想起奧運的日子,天很藍,甚至可以看見星空燦爛,因為北京市與周邊的人煙工廠都停產了,還有什麼力量能使我們的天空真正藍起來,而不是現在這樣,總是灰濛蒙的一片。
這個提早來臨的冬天真是寒冷,雪壓下來,菜價馬上上去了,還好,糧食供應充足。但沒有人自掃門前雪,局部交通阻塞也只能靠時間來緩解危機。有時候,你會發現,政府離你很近,有時候,政府卻離你很遠,遠得你看不見它老去的容顏。政府及時出台措施供暖,可以說是顧及了民意,但億萬富翁潘石屹與建外SOHO上萬業主,卻因物業之間的糾紛而無法供暖,而飽受嚴寒之苦。
政府似乎無力介入其間,進行有效的協調。它的象徵與寓意是深遠的,這是一個新貴群體,而潘石屹則是新貴領袖,他們陷入城市的叢林之中,亦無力自救,社區物業一場糾紛,就完全閒置了業主的權益,你寒你冷,不關物業的事,業主們呢,是一盤散沙,當潘石屹想介入成為組織者,取代物業收集費用以獲得正常供暖時,物業的矛頭就直指潘石屹。經濟力量成為超越業主的主體力量,它的經濟利益遠超過業主的正常生活權益。
說了這些,我不知我在叨些什麼,這就說明,一個城市對一個人形成的莫名焦慮已成為現實。
我所說的一切,我都無法與身邊的城市人一起,去有效校正,為什麼,因為我們沒有社區代表或代言人,甚至我們的業主委員會也形同虛設。說迪拜建在沙漠上,而我們的城市,卻建在沙粒上,市民們都是一粒一粒的沙子,沒有一個有效的能夠處理危機或與政府形成博弈的組織。
上千萬陌生的人、只考慮自己權益的人、無法維護自己權益的人,組成一個巨大的城市,鄰居是誰,不知道。
我們都是自己,只在熟人社會裡生存與交流。
我們推動發鄉村,卻沒有收穫城市。
文章來源:《中國數字時代》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