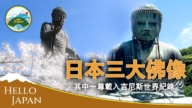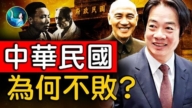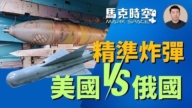重发以前写的一篇文章。也是服毒自杀,也是遗书,我也还是像写这篇文章时一样不确定,她是否适合被讲成一个故事,她也还是我没有穿过的那一个人。
那时候我们班不是留守儿童的孩子可以用两只手数过来,当然,那个时候我们都还不知道“留守儿童”这个词语,后来知道了也很难准确评估这个词语的指向和带来的后果,大家身上的确有很多共性,比如匮乏的物质,缺少关爱,一定程度的心灵封闭,这种共性如今被不断放大甚至绝对化,成为标签。
四个幼童的事件后,大制度层面的讨论不断偏离方向,质疑贫穷程度,质疑救助力度,质疑公益,似乎都触到了点上,又很快被部分地推翻,大失方寸,因为大多数的讨论都只是从固有的预设和想像出发,又缺少耐心。
而回到几个孩子本身,呓语般的几行遗言,没有祈求和控诉,以往的注视框架和焦点都显得无效和苍白,至少对有着相似生活经历的我来说,我是心虚的。
即使是留守儿童,他们也和所有的孩子一样,个体与个体之间决然不同,面对的问题和自己摸索的解决办法也会完全相反,他们身边并没有大人来关照和引导他们的这些不同,而在远方人群的注视和评论里,他们又只是面目模糊而相似的一大群孩子。
正文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邻镇的一个村小学办垮了,班上突然转来一大群孩子,当中有一个很洋气的姑娘叫吴绍英,我们背英文字母表都是“阿波吃的”开头,她读的居然是ABCD。简直惊为天人!
后来才发现,她还有作文书,还会写日记,还会在上课之前预习,上课之后复习,非常让人崇拜。原来她曾经跟着父母出门打工,在湖北某座产砖的小城市呆过。
上课的时候,语文老师说,我抽个人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所有人都把头埋得低低的,听得见邻座跟自己一样心里咚咚跳,突然老师也以一种惊异的口吻说:”那那个新同学来回答一下吧。“全班抬头一看,她竟然举手了。天哪!竟然真的有人会在课堂上举手答问!那以后,我们简直崇拜死了她,觉得她的笑都和我们玩泥巴时傻乎乎的笑不一样,有一种见过世面的爽朗。
我家离学校近,有时会带她到我家里玩。她很羡慕我有一间自己的卧室,我说没什么好的,我的卧室在房子最后面,靠着一个小山包,山包后面就是村里的乱坟岗,晚上老有乌鸦嘎嘎乱叫,吓人得很,开灯都睡不着。她笑着打我说:“你还不知足,有自己的房间了,可以好好看书做作业,也许还能放一个书架呢。”书架?!我想了一下,真是天外之物。
小学毕业的时候,一个同学说吴绍英的妈妈不让她读初中,她很伤心。我很吃惊,虽然她也和我们一样穿着满身起球的尼龙旧衣服,但我还是觉得她家应该是很好的,她成绩挺好,也喜欢读书,没有理由不升学啊。我们那个地方一般人家早过了孩子初中都读不起的阶段。
我问她,她绞着手指嘿嘿笑了一下,说:“可能哦!不过不管了,再说吧。”笑得还挺开心的。
后来,她果然还是跟我们一起去镇上的中心校读了初中,还和另外几个同学一起分到了实验班。初中班上镇上的孩子多,比她更洋气,她就湮没了下去。
我记不得有什么事儿让她很烦躁,除了初一的时候,她比我们都早来月经,每次都痛得满头是汗,晚上要撑著身子去厕所换几次卫生巾,并且每次都要用两个。我们那时候都不懂这事儿,不知道要怎么帮她,觉得月经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她反过来安慰我们,说没事没事,那几天过了就好了。又低着头说:“就是买完那个,攒了两个星期的钱都花完了。”说完一个人嘿嘿笑。
初二的时候,我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突发奇想,把她的名字去了偏旁,叫“召央”。全班都觉得这个名字好玩,就叫开了。“哎呀,遭殃遭殃,呸,真不吉利。”她扭著身子反抗,又笑得开心,嘻嘻哈哈地答应。
谁也没想到不久就出事了。
之后不久是五一节,我们跟初三的毕业生一样早两天到学校补课。那天晚自习已经快上课了,她还没到,开始大家没觉得什么,她家远,要走两个多小时的山路,她平时也常常掐着上课的点才到。以前上小学的时候,他们冬天经常打火把来上学,惹得近一些的学生很眼馋。但那天一直到三节晚自习上完了,也没她的人影,有人笑着说:“召央这回真的遭殃了,又患迷糊,记错了放假时间吧。”老师没她们家的电话,只能问和她住得近的学生,大家都说不知道。
第二天上课,早上第一节课上了一半,给我们上课的班主任突然被叫出去,然后就没进来,只托了一个初三的老师来跟我们说,下面的几节课自习。那天上午阳光特别好,明晃晃的,大家在教室叽叽喳喳地闹。但是第三节课的时候,突然有同学在初三的学生那里听说,我们这个年级有个女生出事了,好像是自杀。
全班都想到吴绍英,一下子就炸了。
中午的时候大家都惶惶不安去吃午饭,吃完午饭看见班主任骑着摩托车从外面回来,我们几个班干部围过去问。班主任坐在那儿,说:“你们等一下。”然后抽了一支烟,才说:“就是吴绍英出事了,服毒自杀。”我一听,一下子想起我给她取得那个外号,突然特别绝望,觉得这件事和那个外号之间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
下午老师都去处理这件事,没人给我们上课,一种很混乱的气息充塞在教室里。有人去翻吴绍英的课桌,里面果然有一个带锁的笔记本,但是撬开了看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就是记录一下每天的事情。但是已经有人在传,说是因为他们家不让她读书了,所以她才想不开。
我很隐约地想起,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有一次中午休息,我们坐在学校后面的树上翻一本早就翻得稀烂的作文书,她突然说:”不读书的话只能去打工,好早就要结婚的,好恼火哦!“我附和着说是是是,心里其实并不懂。
倒是在她出事时,我们已经初二,很多同学开始巴不得不升学,出去打工挣钱,可以买衣服买耳环,可以化妆从街上飘来飘去跟大人平起平坐,可以去城里学上网,可以想说脏话就说脏话。
如果她不出事,我可能永远不会隐约地想起这件事。
那天上晚自习之前,班主任找了几个班干部,说是代表全班去给她坐夜(s守灵),并以班级的名义买了一个花圈和一床被子。
老师们骑摩托带我们去她家,土路很窄,一边就是悬崖,另一边是崖壁,掉了很多的石子在路上,好几次摩托车打滑,似乎要掉到悬崖下去了。走了有半个小时吧,才到了一处有大田坎的地方,老师停下车,带我们再走了一段路才下到山洼底下她家里。
山洼里只有她们家一户人家,平房,红砖上长满了碧绿的青苔,像是随时要颓倒在苍苍山色里,比我想像的要破败许多。
我们去的时候,正在收拾晚饭的席面,一支锣鼓队在堂屋外敲敲打打,到处都是人群,胡乱而热闹。
她的棺材架在两条长凳上,搁在屋前大坝子不起眼的一角,像是跟这场热闹不相关的家具,被挪在一边腾位置。棺材是新的,非常单薄,没有上漆,是奶黄的原木色彩。盖子还没有合上,露出一个三角形的洞,洞里伸出一条深棕色毛毯的角。她小小的身子应该就裹在里面。
我往前走了几步,看到棺材上的边缘还有未磨光滑的木屑。我很去想过去掀开那条毛毯看一眼,班主任一把拉住我说:“不要看!”
这期间,她爸爸过来招呼了我们一下,红着眼睛搓着手讷讷地接了东西,搬了两把椅子过来请我们坐,然后就走开了。他没有哭,倒是她妈妈,被旁人拉着,一直死命往棺材上扑,边扑边反反复复地哭喊:“我的女啊,我的女啊!”
我们人多,两把椅子根本不够坐,大家就一直站着,站了一会儿,天色快要完全暗下来,老师们就去告辞带我们回学校了,并没有真的坐夜。走的时候从她家屋后的小路到坡上去的那一段路,一直听到她妈妈凄厉的哭号,远远地传荡在无边无际的山里。
回去的路上,班主任告诉我,之所以不让我看,是因为她满脸青一块红一块,又在水里泡涨了,怕我看了做噩梦。
回到学校才知道,吴绍英还写了一封遗信,是给她妈妈的。老师拿来念给了全班同学听,她在信里说,实在很害怕去打工,质问她妈妈为什么不公平,要她去挣钱供哥哥娶媳妇。遗书的最后口气软了一些,嘱咐她妈妈以后不要对她爸爸那么凶。其它的我就不记得了。
后来,在家里时我听人说,那天她吃了中午饭就出门了,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到我们读小学的地方买了老鼠药和一包牛板筋,又回到离她家不远的一个山湾湾里,山湾湾里有一个积水潭,她就在积水潭边喝的药。据说牛板筋只吃了一小半。牛板筋5角钱一包,她平时不舍得买。
积水潭背阴,从路上根本看不到潭边有人,但是她把书包挂在了积水潭边的树枝上。第二天早上,有人路过时看到那个平时人迹罕至的潭边居然有一个鲜艳的书包,高高地伸展着,觉得不对劲,走下去才发现了她,身体早已经僵了。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