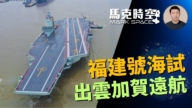【新唐人2012年10月26日讯】【导读】长篇小说《拉面者》是作者马建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后写的政治寓言小说。书中的人物是一位专业作家和职业献血者,他俩彻夜喝酒长谈,聊的大都是周围活得不光彩的小人物的荒唐事。小说里闪现的角色都如面团,被无形拉面者扯来扯去,失去了形状和内心世界,其实这也是中国人的真实处境。然而今天的社会现实,又远比小说更荒诞。
(接上期)
占有者或被占有者
那期待如酒精般渐渐吞噬了他体内的肌理,使他在麻木——伴着局部一些器官的颤抖——中机械地、重复地品尝着。他恍然找到了置身于伊甸园之类的愉悦。
如果没有她的破坏,他的生活也许还会继续,至少还会在那张主编的桌前等候情书如美酒般在上午随邮递员的脚步传进编辑部放在桌上供他慢慢品味、吸吮。
这位文学双月刊的主编自从找到了这条出路,便在每个牛奶般的清晨以优雅的姿势冲一杯茶,捡掉桌面上的头发(是白灰色)。用矜持的动作把那些“主编收”的来信故意先往桌边推一推(注意,所有举止并没有观众,他做给自己看),只用眼角扫扫信堆里某些熟悉或期待的笔迹。往下一些意义不大的动作也要完成:把手指伸到鼻孔往外抠鼻屎并挤出些皱纹,双目与晃动的脑袋不断撕扯(很像猫在吃耗子前故意看着别处),还要把新潮皮鞋脱掉拉开最下面的抽屉踩上,再摆好一张《人民日报》,以防进来的人看到他赤脚。他还要在转椅里晃荡几下,使他矮小的身体发出足够的声音。然后,在不做白日梦的早晨,把脑袋朝椅背靠牢对着天花板。把不再结实的肩膀放松,把润肤露擦在因做饭洗碗而干皱的手上,这才开始拆信。
有时,主编从信的妙境里重返现实空间后还要挤眉弄眼。有文章介绍,这样可以使人恢复青春,至少令面部肌肉充满表现力。这对一个五十开外刚步入情场的人是极为重要的。他还常在上班的路上不断嗑齿,上下牙打得跟步伐一致,这节奏保证他不会走路做梦,还可以美容。
在剪开信件时,他基本能从字迹上分出哪些是来稿,哪些是情信。他有三个抽屉装满了女文学青年写给他的情书。有些是为了能发稿,有些是进入恋爱年龄的姑娘,把写风花雪月的老文人当成人生楷模时出现的异常恋情。而主编近两年常在杂志上发表些“生活的道路是曲折的”、“又是一个黄昏”、“那轻轻吹进心扉的秋叶”之类的诗,骗些多愁善感的少女。他明白骗姑娘只要大谈人生这个道理之后,便在杂志上开辟了“新人新诗”一栏。
寻觅女人要勾引写诗的,千万不能勾引写小说的,他的生活经历已经对女作家产生生理上的恐惧。他还注明来稿要附有照片和简历。这两年,主编已经出神入化了。他还甚至从字迹和照片上就能看出女人们能否掉进他的陷阱。经验大概是:丑女人有才华,在秀丽的笔迹中常透出敏锐的观察力;描写蓝天白云和花花草草的女人最容易上勾,但这种女人身边总有其它男人,不纯粹。他的重点放在一些跟晚霞没完没了的姑娘身上。她们同时喜欢的往往是冬日的小屋、秋天最后一片树叶、泪珠、吻我的那个深夜和咖啡没放糖之类,这种女人相貌平平,失过恋或家庭的纠纷影响她们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他便可以乘虚而入,给她们温暖的“爱”。反正这一类的姑娘足以经受多次被骗或被辱的情感了。只有那个死缠着他不放的纺织女工除外。
清晨,成了主编生命的重要内容,他每一分钟都是投入的。下午四点,他才会开始做梦,一些无关紧要的碎梦。(专业作家常常感觉那些梦和自己的胡思乱想有相同之处,当血客的谈话令他反感或者厌倦时,当领导和他谈话或者开会时,他就常常沉迷在白日梦中。)在这时刻来临之际,主编会假装看稿件,双目死死地或游移不定地落在某个方向。梦,就像个过客,会在抽了一支烟的时间里站起走掉了。
那天下午,他梦到自己行走在粪河里(专业作家在黑暗中苦笑了),这也许是他桃花梦的岁月中必然反馈回来的情景。而在当时,他常把信件中对他恭维的字眼抓出来搬到梦中,品味着在情河里行走的成功感:“世界上惟一的男人”、“真正的高仓健式的男子汉”、“全部的生命里只有你”、“没有你我就不活了”、“才华横溢的天才”、“文坛舵手”、“爱情歌手”。他从充满青春气息的女人味中吸取着精神支撑,并融入自己久不存在的尊严里。
这尊严他曾用尽了平生努力试图从文学中攫回。可他的老婆——专业女作家把他牢牢地钉在了合格丈夫的岗位——在厨房和大堆室内生活日杂用品中间,他稳稳当当地步入了十四个年头。这位身高一点六米的家庭“主夫”在洗碗、扫头发的空隙里也曾不断与梦斗争,试图抓住点艺术的只字片句铺到纸上,可那些努力已过去了。他看清自己无能的笔只能从“情书精选”中挑些句子寄给姑娘们,才能再也不会降到女作家丈夫的头上了。
他是一位出生在有知识的家庭,父亲是位医生,母亲是地方剧团的演员的后裔。青年时代也曾冒过尖,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过三首诗。他描写当地学雷锋标兵赵先进的事迹,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报告文学使他和赵先进一样在这个城市里成了名人,他被从工厂抽出来调到群众艺术馆专抓宣传工作。紧接着,他又迎来了自己一生的高潮,那幸福几乎是从天而降:他看了电影《樱》以后写了一篇叫“故乡情”的散文,把海外归国探亲的华侨“描写”到他们这个沿海城市,电影里的日本来客换成了台湾的。这篇散文立即被中央统战部看中,正是对外宣传的及时雨,随之引来了摄制组、演员、中央特派员,包括两位外国演员。
那些天他成了全市的红人,市领导见他都要用商量的语气。全市的热门话题都是他的剧本和随之而来的“天外来客”。他走在街上常常有不认识的人招呼他,和外地来的演员一样,身后跟着一排排观众。夜晚来临,他的家也和演员们住的旅馆一样围满了群众。记载着那节日般时光的证据依然在他的家里:他和一些演员(包括两个外国的)的合影。当时,那张彩色照片在全市是惟一的。可惜的是当时拍照的地点是医院,他在那个引人注目的季节得了肝炎,而外国人千真万确地去了医院看他。事后他成了讲解那两个外国人的权威。一些看过正面和看过背面,看过头发和看过裤子的人争论不休时,大家往往都说:不信,去问问“甲肝”。他的外号就这样传开了。当医院院长因说了句“黑头发的外国人,不是纯种”而被撤职时,甲肝的照片救了他:彩色照片上外国人的头发是黑的。院长给保留了党籍,调到手术室当了主任。
在那个黄金般的岁月里,她——主编后来的老婆——写了情书,称他为中国的“保尔”,也是她的太阳,她终身追求的伟岸。
甲肝头一次接到白纸黑字上写着“爱你”这种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话,他马上把信交给了前来看望他的市委宣传部长。经过组织调查,她原是当地军区政委的女儿,组织上在短短一星期就把同意恋爱的结果告诉了甲肝,信也给了他,只是组织上把那些下流字眼涂掉了。
她开始来看他了。如果不是因住院发烧的话,甲肝也许能记起,她穿的裙子也跟来到这个城市的女演员赵晓红的一样。
她坐在他对面,两条白腿冻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这里的护士和来过的女人都穿这种裙子。”他当年说。
未来的老婆说:“街上还流行赵大山茄克。”
“赵大山是谁?”他问。
“男演员,那个魁梧的。”
“我没记住他的名字。”甲肝内疚地说。
“连我小弟都知道。”女方对甲肝的无知毫不原谅。
她离开病房总要留下些令他浮想联翩的东西,签了字的书、吃剩的梨核、花露水的香味、头发。他知道她是高干子女时,心里受宠若惊。地位的悬殊不得不令他反思自己的资历:
年方三十六岁,党员,工资四十七块九角,曾被评过车间的先进生产者。这些她大概并不在乎。事业上的成绩给他的安慰最大,他是电影《故乡情》的原作者,还在《中国青年报》和《光明日报》发表过作品近二万字,由于自学成才从工厂调到文化单位转成干部,坐过市领导的红旗轿车,代表车间去东北参观活铁人李国才。这些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她虽然家里有五间房两个厕所,但她的工资并不比他高,而且,她只是小时候去过一次北京而已。想到这些,甲肝心里平衡了,他闻着她留下的气息,对她的爱油然而生,躺在病床上就决定结婚了。
几月后,甲肝有了老婆,同时,群艺馆新创刊的文学双月刊的主编就落在了他头上。他的人生高峰达到了。
但是,好景不常,两年以后,他的老婆急起直追,有两篇小说发表在全国重点刊物上,一跃而成为该市的文学将才,还去北京和黄山开了两次笔会。当他俩双双加入新成立的作家协会并成为会员的那个月,她又当了全市第一个专业作家。每天在家不用上班,由国家发着工资写她的小说。这新事物给甲肝没带来任何好处。他的崇拜者再也不叫他保尔了,而是以大家常用的称呼“甲肝”在家里指挥他。她成了这个城市的青年人感知外面信息的主要人物,她知道北京作家刘国的情人的名字,知道作家史铁生的腿是残废的。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她勇往直前,先是戴上假胸罩,然后就烫了头发,弯弯曲曲像外国人。她看了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北京寄来的《今天》诗刊,开始写起伤感和浪漫的诗。当甲肝把“爱情”落到纸上之时,她已经用“性冲动”了。她和北京的青年诗人通信,用了大量极缠绵的语句,换来了“我的小绵羊”、“遥远的宝贝”和“梦里飞来飞去的小天使”。她紧紧注视着形势发展。
(待续)
【作者简介】马建,山东青岛人。一九八七年因中篇小说‘亮出你的舌苔’而引发了中国文坛的一场政治风波, 其作品被查封销毁,并受到批判。著有长篇小说《思惑》、《拉面者》、《红尘》、《九条叉路》;中短篇小说集《怨碑》;文集《人生伴侣》等。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两千零四年法国的文学月刊‘阅读’杂志第五期,选出代表本世纪的全球五十位作家,马建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作家。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发表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