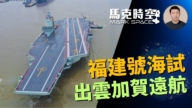【新唐人2011年9月26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一章:陷入阳谋的初生牛犊
第三节:灾难袭来
我和马开先逃避大鸣大放,躲在重大后校园那幢我们选择的“世外桃源”里。但是,民主自由的思潮,使马开先耐不住了。我没有能阻止她在临近尾声的鸣放大会上,含着一腔被激发起来的正义,走上鸣放讲台,讲出在三五反运动中的悲剧,并为董时光叫好。
我们确实没有想到,一张巨大的预设的灾难之网,已经向我们罩来……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按照毛泽东已经定好的“右派分子”框框,以庐郁文收到“恐吓匿名信”为突破口,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一场预谋的浩劫,向神州大地劈空袭来。
才开始走向人生旅途的大学学子们、一群被民主思潮拨动的初生牛犊,陷入了“阳谋”的陷阱。
在重大学生们的心目中,包括那位团支部书记蒲世光,共产党仍是一个威严的“母亲”。他们天真地相信共产党是由“特殊材料”铸成的、是具有伟大人格的优秀分子。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那“闻者足戒”的“诚挚”许诺,原来是一个陷井!
这些天真的孩子们没看出,鸣放动员会上“坦诚相待”的外衣里,竟藏着一张“毒草香花六条标准”的罗网。等他们说出真话后,便被一网打尽了。
学校的“工人阶级”也被组织起来,由伙食团的炊事员、临时工、门卫们组织起来的一支队伍,从民主湖畔出发,沿着环绕学生宿舍刚修好的马路,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他们一路高喊着:“不许攻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右派老实一点!”等口号。
学校的同学都挤着去观看了,随后,各系还组织了讨论。大家心里还不明白,这“右派”们究竟是谁?尤其没想到游行队伍背后的组织者竟是张科长和曹英们。
想在反击右派的运动中立功的人,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反击”火药味甚浓的大字报一张接一张地贴出来。在林毓森张贴那张漫画的位置上,代之以一张巨幅“质问”书。那几幅将张科长画成胖猪,将宋书记画成矮怪物的画已被撕下,并被收藏到校党委的整风办公室里去了。
至于《XX讲教授治校是什么意思?》、《不准XX污蔑党》、《“非团员呼声编辑部”的反革命真相》等大字报更是一个比一个充满杀气。最初被点了名的几位同学,傻乎乎地站在自己贴大字报的地方,感到一场大祸临头了。
有些人刚被推上“右派言行批判大会”的讲台时,就像一群被渔人之网捞起的小鱼,开始还在渔网中蹦跳,声明自己善良的动机,显露出乞求宽恕的可怜相。但哪里再有你“辩论”的余地?他们被主持批判的人喝令“不准狡辩!”只有老实交待,低头认罪才可以求得人民的宽大。
凡被批判的人在开过批判大会后,便要接过主持会议者交给的一叠白纸,没完没了地写“我的检查”。
也有很有个性的同学拒不认罪,我看到在机械系组织的斗争会上,二年级的殷世红同学一直昂着头不说话,开过会以后拒绝写检查,但他立刻遭到了隔离、禁闭。在冶金系批斗大会上,蒲世光面对气势汹汹的几个打手,用冷笑来回答,但他也立即被关了起来。
就这样,早春的暖风迅速变成了寒流,刚刚开始活跃的校园空气,变得更加凝重而沉闷。
我侥幸地躲开了这最初的袭击,这要托我严守了不问政治的"忠告",我既对党天下“麻木不仁”,对“政治设计院”如观海外奇闻,至于《人民日报》上提到李康年的赎买二十年;黄绍竤的批评“以党代政”更是从未研究,就连在松林坡礼堂董时光的报告,我都没去听。
因为我远远躲开了大小鸣放会,所以我也暂时躲脱了“秋后追查”。当各系将一个多月前鸣放大字报的照片作为“毒草”刊登出来,我才惊叫:“好险!”
机械系的年级党小组,在支部宣传委员曹英的组织下异常活跃。曹英到学校来与其是求一技之长,不如说是共产党在学校中的统治骨干,他们班上说他几乎没有一个学科是及格的,他的专长就是“整人”。
此时凭着他多年干“革命”的嗅觉,正是“接受党的考验”,完成“党交给的特殊任务”,为他今后平步青云创造良好条件的时候,这种机会岂可放过?
他这些日子特别忙碌,系里的批判会几乎都由他主持,将在大鸣大放中提了意见的老师和同学,一个个推上批斗台。
马开先没有幸免,她被曹英叫去做了特别谈话,她是青年团员,得按六条划定毒草的标准,对照着自己的言行写出检查和认识。曹英威胁她说,所有在董时光鸣放会上跳出来攻击党的人,都将受到严肃的处理。
马开先不愿屈从,突然向机械系主任呈递了退学报告。
她收到了她父母的回信,父母认为她之所以如此,全是受了我的影响。她的哥哥在给她的回信中,明确要她立即断掉同我的恋爱关系。在他们看来,她之所以会如此“反动”,全是受了我的影响。
得知她要退学,我坚决反对。我们之间便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她认为:现在读书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她也无心读书。我则认为,不读书,何以在这个社会中求取生存之地?
一天下午,我几乎强拉着她到松林坡我们系主任钱企范的家里。钱教授也劝她回心转意安心求学,可生性倔强的她并没有被说服。当我们从钱教授家里出来以后,我出奇不意地向她表示:“如果你要退学,我们就此决裂。”
一句戏言,不欢而散。唉,我刚撞进了情场,哪里懂得爱情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甜果,一不小心就被摔坏了。
后来,我的不幸遭遇使我明白,马开先的退学选择恰恰是正确而明智的。可惜,悔之晚矣。
放暑假,我独自忧伤地回到北碚,在车站分手时,她说她去城里姑妈家暂住一段时间,在学校没有批准她退学的申请前,当然还得回校。
弟弟迎出来了,接过行李,兴冲冲地喊着外婆。外婆闻声走了出来,照例用她那慈祥的眼睛,仔细端详我,用她那粗糙的手抚摸着我的头,笑着说:“你比寒假回来的时候瘦了。”
母亲依然心事重重,虽然四年前她与父亲正式办了离婚手续,但她没有能力抗住社会的压力和良知的责备。这些年来,她从没给父亲写信,也不知道他的下落,但内心常常自责,有一种负罪感,这使她经常做恶梦。
父亲被判刑的通知书和判决书,我们一直没有收到,开始我们还去法院怯生生询问过,但法院拒绝回答我们,并说他的情况,你们家属无权过问,面对这种无理拒绝,我们就再也不敢问,更从来不敢抗议。
直到二十四年后,我写了数十封信,寻找父亲的下落,才由四川省公安厅发给我一张巴掌大的回函,告之1956年5月6日父亲因病死于西康一个伐木劳改营。
(一)躲不开的阳谋
1957年,母亲终于在大鸣大放的“和煦春风”中,突破了沉默多年的心理禁区,小心翼翼的向托儿所所长倪佩兰讲起她对丈夫“反革命案件”的怀疑:不是说革大学习以后,他的所有历史问题都交待了吗?作为“班主任”的邓小平不是在散学典礼上向他们宣布:“你们终于丢下沉重的历史包袱,从此可以轻装上阵,参加革命的队伍了吗?”不是曾许诺让他充任当时十分稀缺的大学教师么?政府的政策怎么就突然变了呢?
还有,那“反革命活动经费”就纯属子虚乌有了,那家庭的积蓄怎么被当成了“活动经费”呢?
母亲在大鸣大放中的这几句疑问,使她钻入了毛泽东的“阳谋”圈套,让她付出了一生的惨重代价!
我回来后不几天,周生碧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在那里还有张世模,这些年龄上属于我长辈的人,是看着我长大的。她们不得不从心底里承认,在所有托儿所家属的孩子中,我是最勤劳、最刻苦,也是最乖的一个孩子。
入学重大以后,她们改变了过去的眼光,表面上非常客气,相见时显出一种尊重来。但我在她们面前始终保持着一种“战战兢兢”的谦恭。
“我们找你来是想向你了解一些情况,也让你来参加对你母亲的帮助。”张世模说。“你妈妈在鸣放期间给你写过信吗?”
周生碧抽出钢笔,开始在小本子上记起来。我点了点头,并没有领会她们的意图。“这些信谈到你的父亲了么?”张世模接着问,用狡狤的眼光盯着我。我迟疑了一下,又点了点头,但不明白问这干嘛。
“你妈一共给你写过多少信?”
她们想调查什么?
我想到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那不都是一些来往的信件么,心中一愣。
母亲确实把她对父亲被捕的种种疑虑,以及她在鸣放会上的发言写信告诉了我,但那又怎么构成犯法了呢?我如实回答:“大概有二、三封吧。”
张世模带着显然是装出来的“宽慰”和“鼓励”对我说:“小伙子,你已是大学生了,前途远大,好好读书,对你母亲要帮助她一下,旧社会的人常钻牛角尖,脑筋转不过弯来。”
她们的盘问使我莫名其妙,十九岁对于我真是太懵懂了,我绝没想到一场横祸已经悄然逼近。
回到家,外婆笑眯了眼睛,在她看来,一家四口人,两个外孙,尤其是我,是她生命的寄托和延伸,她是可以为我俩付出一切的。
(二)我的外婆
自幼父母亲很忙,很少管过我,我的生活起居全是外婆呵护。晚上,我都是睡在她的脚下。
1957年的那个暑假,她叫我坐在她的身边,唠叨着那些不知重复了多少次的故事,讲我是怎么难产降生在南京鼓楼医院中,讲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讲我因为医院护理不当几乎窒息死亡,讲如何从炮火连天的南京逃难出来,从遍地尸首和弃儿堆中,抱着我拚命挤进逃难的人群……
她苍白的头发蓬乱地散盖在满布皱纹的脸庞上。我发现她真的已经很老了,背也越来越驼。
说到她的驼背,她便会述说当年的艰辛:“抗战时,我们一家人从南京逃到重庆,经济窘迫,在上清寺租了一间阁楼。那阁楼又矮又黑,平时人在里面是直不起腰的,只是价钱便宜,每月只付五个铜板。白天,你爸妈整天在外奔波,家务活和你全扔给了我。你小时候托妈的福,她奶水特别好,你长得又白又胖,但是你白天非要人抱,于是我就只好成天弯着腰一边背着你,一边洗衣做饭。半年下来,我的背就开始驼了”。
她讲述这些脸上全是幸福。
每当我注视她佝偻、苍老的身躯,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惜。她青年守寡,中年跟随女儿颠沛流离,操劳终日,从来没有过过气派的悠闲日子。我握着她那长满老茧的手,轻声而自信地对她说:“外婆,你为了我们兄弟俩劳碌了一辈子,从没享过福,等我大学毕业,我一定把你接在我身边,给你专门找一间舒适的房间,好好地过几年快快乐乐的晚年生活。”
她笑了,眼里含着泪花。
二十多天的暑假,我的心情始终是阴郁的,面对着犯愁的母亲,心中老是压着一块石头。
我不时想到马开先,想起她对生活的绝望。若不是这场“大鸣大放”,我们本打算在这个暑假同车回北碚。她的姨爹和姨妈在西南农学院任教,她可以住在她姨爹家,趁着一个多月的假期,一同去缙云山和北温泉,痛痛快快地玩。
可现在一切都被打破了,假期她竟忙着办理退学手续,今后我们的关系也不知会发展成怎样。
因为心境不佳,我提前了五天返校。弟弟帮助我收拾东西,外婆不停地唠叨冬天的衣物要带好。她好像有一种恐惧的预感,一再地提醒我,在学校不要乱说话,不要同人吵架。她拄着拐杖,一直拉着我的手,颤抖着把我送到那竹篱笆做的小门外。
当我跨上马路,她突然把我叫到她身边,一再地抚摸我的头,我情不自禁将身俯下,把我的脸贴在她那苍白的前额上,吻了吻。我感觉到她热乎乎的泪水顺着脸夹向我的脖子里流。
到了拐弯的地方,我又回过头去,她的身影还一动不动地伫立在那木门边。这一幕像永远不能褪去的底片,储存在我的大脑中,跟了我一辈子。
我对她许下的诺言,也许正是她盼望了一辈子的梦想。但是,它终于成了泡影。而这一别,也成了我和她饮恨一生的永诀!
(三)马开先
回到学校,刚刚跨进寝室,正碰上留校“工作”的郭英华,她诧异地看着我,问道:“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马开先呢?”我吃了一惊,预感到发生了什么,回答她:“我怎么知道她上哪儿去了?”
“你们吵架了吗?放学那天你们不是一起离校的吗?怎么她那天晚上独自回来了?还酗酒大闹了一场,学校正在追查这件事。”
我说:“我们确是一起出校的,但到了车站,她说要上姑妈家去,便分手了,后来,我就再不知道她在哪儿。”
郭英华便把当天晚上发生的事,向我一一叙说。
那天晚上大约九点钟,马开先提着一瓶白酒和一包糖果独自一人回到了她的寝室并关上门窗。不一会,屋里传出走了谱的歌声,沙哑而不清,但听得出是“丽达之歌”,接着是一阵狂笑,狂笑后又是一阵哭声,后来传出了玻璃摔碎的声音。
有人从门的一条细缝向里看,只见她满脸通红,手舞足蹈在那里“跳舞”。一瓶白酒只剩下了半瓶,酒杯摔碎在地下。
门外的人拚命射门,但无济于事。不一会,里面突然静下来,郭英华赶紧到男生寝室找来陈思和刘大奎。踹开门,只见马开先正大口大口呕吐,屋子里充斥着酒味和发酸的臭气。
听到这里,我知道悲剧终于开始了。我连忙到她的寝室去,在她的课桌前呆坐。
她酗酒和狂舞是因为我吗?女孩子真有这样脆弱吗?她究竟到哪里去了?我上哪儿去找她呢?这时,我的心里再也无法平静,我想得很复杂,她是出走还是自杀?
我决定要先找到她的姑妈。想到这里,我便打开她抽屉,寻找她收到的信件。信件提供了重庆城里的两个地址,一个是黄花园某巷10号;一个是在枇杷山公园。
我匆匆走出校门,坐上了开往牛角沱的公共汽车。到了牛角沱,便下车步行。我按信封上的地址,边走边问路,整整在城里找了四个小时,下午四点钟,我终于在枇杷山公园下街的某巷中找到了她姑妈。房主人打开了嵌在围墙中间的小门,里屋竟传出了马开先的声音。
她穿着一身白色连衣裙,从楼上迎了下来,看到我,她十分惊喜,接着带着歉意地说:“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一块空悬的石头终于从我的心里落地,我装出神秘而顽皮的样子说:“我有特异功能,随便你跑到天涯海角,我也会把你找出来。”
我在车上准备好的那些道歉话全部吞了回去,两个人的误解也立刻冰释。
“你吃饭了吗?”她问道。此时我才感到饥肠辘辘。从早上北碚出发到现在,整整九个小时的奔波,疲劳和饥饿竟在这一连串怪诞的过程中忘得干干净净。
那天晚上,阿先主灶,饭菜很香,我们吃得很开心,我也得了教训,暂时对阿先退学的事缄口不提,也没有问她那晚何以酗酒狂唱?她的姑妈对人挺热忱,看不出她是不是同她的哥、妈一样,反对我和阿先的初恋?
晚饭以后,我和阿先漫步在临江的公路上,凭着石栏望去,嘉陵江蜿蜒如带,两岸分布在岩壁上的建筑点点灯光,映着月色,立体的构成一幅很有诗意的图画。
重重愁绪又重新涌上我的心头,母亲的忧郁重新爬上我的心扉,我看着面前的这个阿先,江风拂动着她的白色连衣裙,显得动人而潇洒。
我希望第二天她能同我一起归校,但是她拒绝了。看来,我昨日的辛苦并没有动摇她退学的决心。
学校并没有如期上课,自习占去了大部分的时间。国庆节刚过,团结广场召开了由千余名大学生组成的下乡支农的誓师动员大会。第二天大学生们便开赴井口参加挖水堰的“劳动锻炼”。
下乡支农的劳动大军一走,秋天的校园空荡荡的,几场连续的秋雨之后,更显得寂寞苍凉,一种积郁在我心中很久的不详之兆,越来越近地向我围拢。
终于有一天,陈思把我叫到一个僻静的教室,语气严峻地对我说:“你必须认真反省在大鸣大放中我的思想言行,包括与母亲的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行,也包括与马开先的言行。”他还说:“你要看清形势,争取主动,党的政策摆得很明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凡是在鸣放中有过错误言行的都要彻底弄清楚,予以批判帮助,决不能存在侥幸心理蒙混过关。”
紧接着他用严肃的口气警告我:“组织上已经掌握了你的情况,这次井口劳动没有叫你去,就是给你充分的时间反省和交待自己的问题,早交待比拖延好,不交代就等于顽抗,性质是可以变化的,希望你争取用人民内部的方法解决你的问题。”说完他给了我一叠稿笺纸,那纸就是一年多前在反胡风运动中曾用过的,用来让有问题的学生写交代的那一种。
我接过稿笺纸心里一阵紧张,现在,我终于不得不改变我原先的态度——置身运动之外而自乐了。
不久,我收到了弟弟给我的来信,告诉我是母亲叫它写的,他说母亲已在组织的监督下。周生碧警告她说,这一段时间不准向重庆大学写信。
我立即找到了那本《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小册子,翻到香花毒草区别的六条标准一一对照。我个人在鸣放中并没有在公开场合下发过言,更谈不上右派言行。
我不知母亲是不是犯六条中的哪几条。是分裂了人民、破坏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破坏削弱了人民民主专政、破坏削弱了民主集中制、摆脱和削弱了共产党的领导,还是损害了社会主义国际团结?
我想,即使母亲在鸣放中对父亲提出了几个政策上的疑问,也够不上这六个破坏和削弱的大罪呀。
至于马开先,她在鸣放时说了什么?党天下?教授治校?对照六大标准似乎只有涉嫌摆脱和削弱共产党领导那条了。
在我看来,纯洁无邪的马开先怎么也不可能同“老谋深算”、“阴险毒辣”的资产阶级右派扯在一起。这么一想,我紧张的心态开始松弛下来。但是,母亲忧伤的面容又浮现在我眼前。陈思的警告又使我的神经绷紧了。
从开学以来就一直没有见到阿先,我是直到在下乡劳动队伍中,才看到她的背影。看来,她是在故意躲避我了。她为什么一直躲避我?阿先啊,你可知道,我现在也陷入了麻烦。我是多么想你,多么需要你给我安慰和鼓励。
(四)荒唐的辩解
我忽然想到了该写信了。
第一封是:“开先,你知道我母亲的痛苦吗?父亲被捕以后,她一人负担着四口老小已不容易,加上反革命家属的精神压力,她终于选择了同父亲离婚。她年轻时就已经在教育事业上显示才能,她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这一次大鸣大放,本想向组织说清多年积疑,消除认为她包庇自己丈夫的怀疑,这样提出来,没有别意。”
我这封称谓马开先的信,是寄给母亲单位上看的,张世模不是在寻找我和我母亲在最近一段时间的通讯吗?让张世模看到这封我给女友的信,更能为母亲辩诬。
第二封是这样写的:“妈妈,你好吗?外婆和弟弟也好吗?整个暑假我的心情都十分沉重,当我返回学校时得知马开先因误解了我,伤心过度,竟然酗酒伤身……我真地感到对不起她,她是真爱着我的,她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孩,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到现在还转不过弯来,开学以后,我一直没有见到她,心中非常挂念,我不希望她辍学,那前途全毁了,后果不堪设想,一个女孩子单独流到社会上闯荡该有多么危险。妈妈,我求你,劝劝她吧,也许她能听你的话,让她去掉那个荒唐决定吧……”
这封称谓妈妈的信,却是寄给马开先的。
两封信,当然要张冠李戴颠倒了寄,称谓开先的信,信封上写了母亲的地址寄给了北碚托儿所,而称谓妈妈的信笺却装进了寄往井口的信封。
这两封信里面包含了多少无奈。倘若当年我就看清了毛泽东心狠手辣的阳谋,我也不会那么可笑地“表演”。
信寄出以后,我心情放松了许多。
日子也真难熬,才两个月的日子就像过了几年,发出的去的信一封也没有收到回信,于是我又担心这些信是否寄到了收信人的手中。到了十二月初,我又提笔写了内容与手法与前面完全相同的两封信。
这次,寄往北碚的信终于有了回音。
(五)同弟弟的最后团聚
1957年12月中旬的一天,大约上午11点钟左右,弟弟突然出现在我寝室的门口,他的到来,给我孤单悲伤的心吹来了一阵暖风,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忧虑。他手里拎着一个黄色的布包,怯生生地站在门口。见到他,我慌忙站起身来,紧握着他的手,那手是冰凉的。
“你什么时候来的?”
“今天一大早。”
屋里还坐着其它人,不便多说什么。
他打开黄布口袋,说:“这是外婆关照带来的,天冷了,外婆叫你注意不要生病了。”口袋里装着一双旧毛线打织的毛袜、一双新布鞋,还有一张用手帕包好的二十块钱。见到那毛袜,我就知道那一定是她戴着昏花的老光眼镜一针一针织出来的。
中午时分,我便同他去学生食堂吃了便饭,然后牵着他的手,从后校门慢慢走到小龙坎医院,当时我的痔疮结痂还没有合好,那儿还留着我的病床。
小小的病房没有其它人,是我们兄弟俩谈心的好地方,弟弟坐在床前细说我走以后发生的情况。
“自从你走以后,托儿所一连开了许多天批判会,妈妈和陈玉如两个成了批判对象。妈妈的主要问题就是替父亲翻案,会上会下追她交代,特别追问同你的联系,说什么串通大儿子订攻守同盟。上星期起正式给妈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规定她今后外出和投信都必须事先告知组织”。
弟弟说得很慢,像是被什么东西堵着喉,边说还边痛苦地思索。
他才十三岁,从他呆滞的目光中,我看到了他嫩弱心灵上的阴影和莫名伤害。
妈妈会被划为右派,从假期中周生碧的态度和语气中我早就听出来了,本是预料中的事,所以也不太惊诧。
弟弟接着说:“昨天下午,外婆把那黄口袋交给我,还给我五块钱作车费,叫我马上到你这里来一趟。她说:家里情况不好,要你不要回家,也不要再写信回来,她说你的信被周生碧拿到会上当作死不认错的证据。外婆还关照你就在学校过年,好好注意身体,不要同人多说什么。”
弟弟讲完,我们两人都沉默不语,心中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脑子里一片空白。
天渐渐暗了下来,我忽然想到,过不了几天就是新年了,今年过年肯定不能回家,便建议说:“今晚我们俩上馆子,算是提前团个年,晚上就同我在病房过一夜,明早我送你上车回北碚。”
弟弟眼里闪了一下,点点头说:“好,今晚我们过年”。
我们兄弟俩手牵手,朝土弯方向走去。我们进了一家饭馆,选了一个窗口临江的座位。既是过年,自然要“奢侈”一点,我破天荒地点了五个菜,是弟弟平素最爱吃的砂锅鱼头、蒜泥白肉、白砍鸡、烧白,还要了一小杯酒。因为舍不得剩下,便慢慢地吃,整整吃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把五盘菜全部吃光。
吃完晚饭,我们两人紧紧地靠在一起,踩着石板铺成的人行道向沙坪坝逛去。我俩投在路面上的影子渐渐拉长又渐渐缩短,远方隐隐传来如诉如泣的“拉茨之歌”。在一家卖副食品商店的门市部,我买了一小袋花生米、一袋水果糖,一小袋桃酥,仍装在弟弟带来的黄口袋中,嘱弟弟明天带给外婆和妈妈,关照他们,我在这儿一切都好,请他们不要牵挂……。
十点钟左右,我们回到病房。那晚,我们兄弟俩和铺而眠。他已经很累,不一会便入睡,我却怎么也睡不着,望着他童稚的脸,万般愁绪涌上心头。打开临江的窗户,嘉陵江的江风令人清醒、令人断肠……
我没有料到这是苍天安排我们兄弟俩最后的一次相聚,第二日车站的离别竟成了我们俩的生死永诀。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