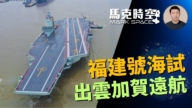【新唐人2012年7月27日訊】得知君立先生的博客文集《中國盒子》要出版了,心裡很為他高興,不過在高興之餘又不免擔心起來,以當前的輿論環境,要想把君立的文章完完整整地呈獻給讀者可能還有些困難。果不其然,之後君立先生告訴我,書稿在審查的時候遇到點問題,一直通過不了,現被打回來讓其修改,弄得他不甚其煩。
君立先生為本書取名為「中國盒子」,書中第一篇文章的標題也是「中國盒子」,想必是要表達某種不便明說的寓意吧。在《中國盒子》一文中,君立寫道:「崖山之後無中國,暴力通吃使一個曾經文化文明的中國重新倒退到弱肉強食的叢林時代。最不幸的是,這種倒退在女真人的天朝再次得到了鞏固和加強……中國傳統體制與中國盒子一樣,是一種反智的產物,但總試圖以美輪美奐的『皇帝新裝』來掩蓋這種反智。」
「盒子」或許不是一個大眾化的詞彙,但「天朝」卻是時下的網絡流行語。在這裡,君立先生用一種巧妙的方法把自己對「盒子」的感情表露無遺,這不禁讓我想起了魯迅口中的那個「鐵屋子」。
1912年,魯迅遷住北京,但生活並不如意,終日生活於苦悶與徬徨之中,靠抄寫殘碑拓片來打磨時光。一次,好友錢玄同前來拜訪,發現魯迅案頭堆滿了古碑抄本,便責問他「你鈔了這些有什麼用?」魯迅沒有直接回答朋友的提問,而是環顧悶熱的陋室,無不悲苦地問道:「中國原本是一個沒有門窗的鐵屋子。假如這座鐵屋子萬難破毀,裡面又躺著許多熟睡的人們,這些人最終都要被悶死——在不知不覺中由昏睡轉入死亡,誰也感受不到痛苦和要死的悲哀。現在你大聲喊叫起來,驚醒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讓他們儘管醒來卻依舊無可逃脫,讓這些人知道痛苦和將死的悲哀,而你又無力拯救他們,這究竟是仁慈,還是殘忍?」
魯迅一直以犀利言辭和錚錚鐵骨著稱,而當時的他也竟然如此失望和悲觀,可見其對中國的絕望到了何種不可言說的程度。一百年後,如今的中國又有哪些改變呢?改革開放或許為這個沉悶的鐵屋子打開了一扇窗,自由的空氣或多或少地飄散了一些過來。於是,人們又開始山呼萬歲,忙不迭地論證鐵屋子的必要性和特殊性,並拒絕讓人們走出屋子。對此,君立先生以其獨特的視角、成熟的筆觸和滿腔的悲憫為這個鐵屋子裡的人又一次發出吶喊的聲音。
在書中,君立先生不是一個道德的說教者,也並非一個民主的鼓吹手,他只是用自己簡單的文字和獨立的思考描述著這個盒子的血腥與無情,殘酷與冰冷——「在傳統時代,殺人償命被認為是最基本的法律信條,但在盒子時代,這一『天條』已經被徹底顛覆……奴隸時代的權力、農業時代的思想、工業時代的商品、信息時代的技術,這四者跨越時空隧道,詭異地在盒子中國雜交並存。」
盒子固然可憎可惡,而在裡面卻又渾然不覺的人何嘗不是可悲可恨呢?面對有形的盒子,單個弱小的我們或許無法與之正面碰撞,但面對無形的盒子,我們應該有勇氣與之抗衡的呀。有形的盒子可以囚禁我們的肉體,但無形的盒子為什麼能禁錮我們的靈魂呢?
在八九年後,這個盒子居然能屹立不倒,並以一種空前自信的姿態嘲諷著所有曾經反抗或詛咒過它的人們,這對於自詡為「勤勞勇敢的中國人民」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羞辱。在這個恥辱的國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在歷經羞辱之後選擇了一條「奇蹟」之路。這個「奇蹟」的背後是精英們與統治者的共謀,懦弱犬儒的精英與精明兇殘的統治者締結成一個創造「奇蹟」的聯盟。爾後,中國「奇蹟」便不斷刷新著世界紀錄,讓全球在瞠目結舌的同時也讓世界見證了一個時代的沒落與荒誕、滑稽與不堪。
在這個不堪的年代,我們拒絕回憶,害怕紀念,前輩們孜孜以求的道義正淪為精明者眼中的笑柄,而同學的鮮血也逐漸成為投機者嘴裡饅頭上的作料。血腥使人恐懼,以至於讓大家蜷縮在盒子冰冷的角落裡瑟瑟發抖也不敢叩擊外面的世界;暴力讓人沉默,所以大家對於身邊的罪惡往往熟視無睹。在這個盒子裡,每一個人既是體制的受害者又是罪惡的共謀者,在這個幽暗無光而又寒氣逼人的環境裡,「難得糊塗」升格成為人處世的「大智大慧」,而於丹式的心靈雞湯則成為繼成功學之後的又一顯學。
面對這個恥辱的國家和不堪的年代,嚮往自由的人們或許顯得有些無力、無助和無奈,但只要人們還有思想,那就還有希望,正如錢玄同對魯迅所說「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我始終堅信:在造物主面前,人人生而平等,每個人都應該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在盒子裡,我們或許沮喪、恐懼和悲觀,但只要我們從我做起,從身邊的小事做起,那就算再固若金湯的盒子也有坍塌毀滅的一天。為了這一天能早日來到,身處盒子裡的我們唯一能做的是儘可能讓自己的思想和靈魂飛出盒子,做一個獨立思考的「盒子外的人」——拒絕謊言,直面良心,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
當我們的思想和靈魂克服恐懼和懦弱而飛出盒子後,我們會欣喜地發現,原來我們所膜拜、所害怕、所畏懼的那個盒子早已破敗不堪、搖搖欲墜,在時代的浪潮的拍打之下,盒子的根基已然侵蝕下沉,盒子的喪鐘早已隱然敲響。
自由從來都不是自上而下的恩賜,只能是自下而上的爭取;民主也非統治者俯身傾顧地作秀,而應該是民眾親身實踐地體驗。儘管盒子可能越修越漂亮,越修越具有迷惑性,以至於我們都有一種把它當家的幻覺,但盒子再漂亮、再安全,它仍舊仍是禁錮我們的那個盒子,這就如同牧場裡的草再豐盛、再鮮美,但羊群依舊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風箏飛得再高它都是不自由的,小鳥飛得再低它都是自由的。中國人不應該只配享受盒子裡的安全和自由,在我們成為中國人之前,也是作為人類的一員而來到這個世界的,所有的中國人生來也都是人,大家都有生存的權利,都有希望的權利。
在詹姆斯·麥克特格(James McTeigue)導演的電影《V字仇殺隊》的結尾,無數個戴著面具的市民面對荷槍實彈的軍隊,依舊義無反顧地走出家門,如潮水般湧上街頭,見證議會大廈的毀滅。英國人最終拿回了屬於他們的東西,親手埋葬了那個具有政治象徵意義的盒子——議會大廈,而這一切都源自於那個戴著面具的V,一個生活在盒子之外並敢與之反抗的人,在他離開這個世界之前,面對秘密警察的子彈,他毫無懼色地說:「在這個面具之下的,並不是一個軀體,而是一種思想,思想,是不害怕子彈的。」
誠哉斯言。如果說權力是有權者的思想,那麼思想便是無權者的權力。面對前現代化的中國,我們或許有一萬個藉口為自己的懦弱和膽怯開脫,但我們一定也有一萬零一個理由讓自己戰勝懦弱、克服膽怯,因為,我們要做的很簡單——只是做一個盒子外的人。
文章來源:《博客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