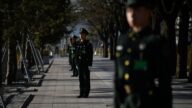【新唐人2011年4月4日訊】【導讀】中共革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得益於共產國際和蘇聯的幫助,這或許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但共產國際和蘇聯究竟給了中國革命,特別是給了中國共產黨人哪些具體的幫助,這卻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問題。從噎發現的各種文獻記載看,過去流傳的關於遵義會議以後,特別是抗戰以後,蘇聯和共產國際也不再信任中共,不再援助中共的說法,是過於簡單化了。事實上,自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開始決定撤出江西中央蘇區之日起,在共產國際和蘇聯軍事及情報機關內部,就迅速開始提出和醞釀著一個用於直接援助中共紅軍的跨國界的行動計劃了。這個計劃最後儘管因種種原因而未能完全實現,但它的存在及其實施經過,足以說明蘇聯和共產國際至少這時並沒有放棄大力援助中共革命的想法。
同樣的情況,我們也不能簡單地得出中共中央自從1935年1月召開遵義會議,成立了新的中央領導機關以後,就不再接受共產國際的指導和幫助,一意堅持獨立自主,一切自力更生了。中國和蘇聯有著上千公里的共同邊界線,幾乎任何稍有頭腦的政治家都能夠看出,蘇聯強大軍事力量的存在和這一便利的陸路連接條件,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來說可能意味著什麼。雖然,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共由此得到的幫助,在數量上還遠不如馮玉祥、盛世才,包括孫中山、蔣介石這些國民黨人或地方軍閥得到的多。但是,這一方面和中共早期過於弱小有關,一方面也受到中國政治環境,包括地理位置的影響。已知1933年蘇聯就曾具體提出和計劃過由海路,甚至通過飛機,向中共江西蘇區運送軍火、藥品以及其他物資的方案,並且設想過提供大筆經費從福建十九路軍手中購買重型火炮、飛機等裝備的方案,只因為當時紅軍具體條件限制,和南京國民黨軍隊圍剿大軍集結太快而未能實現。《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給李竹聲的電報》,1933年10月12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皮亞特尼茨基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電報》,1933年10月24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給埃韋特的電報》,1933年10月29日;《皮亞特尼茨基給埃韋特的電報》,1933年11月2日;《埃韋特給皮亞特尼茨基的電報》,1933年11月14日;《皮亞特尼茨基給埃韋特的電報》,1933年11月18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第545、559、575、585、618、623頁;《皮亞特尼茨基給埃韋特的電報》,1934年4月26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給李竹聲的電報》,1934年5月26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4),第118、123頁。然而,在1935年,當紅軍長途征戰,最終選擇北上,開始靠近蘇蒙邊界的時候,這樣的援助條件第一次變得現實起來了。據此,莫斯科很快依據過去幫助馮玉祥國民軍的經驗,作出了通過中國西北邊境大規模援助紅軍的重要決定。於是就有了紅軍「打通國際路線」的浴血征戰。如果中國共產黨人這一次而不是在十年之後的1945—1946年取得了蘇聯的援助,中共革命後來的歷史很可能會大不相同。
孫中山、馮玉祥、鮑羅庭都曾嘗試從西北接取蘇聯援助
在中國近代歷史上,人們至少曾經三度提出過從西北邊境接通蘇聯,接取援助的設想。一次是在20年代初,當時孫中山發動的革命歷經挫折,俄國布爾什維克政權抗擊十四國武裝干涉,逐步將其統治擴展到遠東地區,孫中山向蘇俄在中國的代表明確提出了一個通過新疆或外蒙接取蘇聯援助,建立革命軍隊,再大舉進攻北京政府的「西北軍事計劃」。為了這個計劃,蔣介石1923年秋天曾經受孫中山之託,率團訪問過莫斯科。但由於國民黨人在西北地區沒有一塊落腳之地,孫中山、蔣介石設想的利用新疆烏魯木齊和蒙古烏蘭巴托(當年叫庫倫)建立軍事基地,組建軍隊,發動進攻的計劃,不僅需要蘇聯紅軍的幫助,而且直接涉及蘇聯與新疆和蒙古的關係問題,因此,蘇聯軍方反覆研究后,拒絕了這個計劃。參見拙作:《孫中山的西北軍事計劃及其夭折》,《歷史研究》1996年第3期。
重提這一設想是在馮玉祥的西北軍開始與南方的國民黨攜手之後的1925年。儘管當時的馮玉祥遠不如南方的國民黨更讓俄國人放心,但考慮到馮玉祥直接在同敵視蘇聯的張作霖作戰,因此,當馮玉祥提出希望能夠通過外蒙古接取蘇聯援助的建議后,莫斯科方面立即作出了積極的響應。僅半年多時間,馮玉祥就至少得到了價值數百萬盧布的388萬支步槍、60門大炮、3架飛機,以及大量彈藥及藥品等參見楊雨青:《國民軍與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從而使一度在與張作霖的奉系軍隊作戰敗北的西北軍,很快發展強大起來。
第三次提出從西北接通蘇聯的想法,是在1927年的4月。當時還在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期間,因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事變,成立反共的南京政府,汪精衛領導下的武漢國民政府雖繼續贊同國共合作,軍事上卻開始漸入困境。於是,當時的蘇聯顧問鮑羅廷明確提出,應當考慮用武漢政府領導下的軍隊繼續向北推進,爭取佔領平津及張家口,「打通國際路線」,取得蘇聯援助,再回過頭來收拾蔣介石。但一來這一主張自始就受到多數激進的共產黨人的反對,認為是「逃跑主義」;二來當時國共分裂已是大勢所趨,實行這一計劃幾乎沒有條件。結果,計劃沒有實現,在共產黨人內部,「打通國際路線」的提法反而背上了一個不大好的名聲。參見拙作:《關於蘇聯、共產國際與中國大革命關係的幾個問題》,《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
兩河口會議確定北上方針,意在背靠西北,逐鹿中原。
中共黨內重新提到「打通國際路線」問題,據說是在1934年。在張國燾出版的《我的回憶》一書中,是這樣說的:在紅軍一、四方面軍會合后雙方領導於1935年6月間舉行的一次會議上,首先由毛澤東提出了向甘北寧夏北進的軍事計劃。他說明共產國際曾來電指示,要我們靠近外蒙古,現在根據我們自身的一切情況,也只有這樣做。我即發問:共產國際何時有這個指示?張聞天起而答覆:在他們沒有離開瑞金以前(約十個月前),共產國際在一個指示的電報中,曾說到中國紅軍在不得已時可以靠近外蒙古。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北京,中國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第226頁。
張國燾記述的這個會議,從時間、內容及事後決議看,顯然是中共目前史書所記的6月26日在懋功附近召開的「兩河口會議」。但查此一會議記錄卻頗多出入。首先,會議提出軍事報告和北進計劃的是周恩來,而非毛澤東。其次,會議上無論毛澤東,還是周恩來或張聞天,都未曾提到共產國際的這一指示,並且也沒有人提到過向甘北寧夏北進的任何想法。可見,是否存在過張國燾所說的這個共產國際指示,值得懷疑。實際上,中共中央撤出江西蘇區后提出過的一系列建議根據地的目標,都在西南地區,如川西南、川西北、四川、川滇黔、貴州、滇東北、川西等。分別見陳雲:《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遵義會議文獻》,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頁;《中央軍委總政治部關於我軍渡烏江的作戰計劃》,1935年1月20日;《中央軍委關於在川黔滇創造蘇區的指示》,1935年2月16日;《動員全體紅色政治工作人員爭取新的勝利》,1935年3月5日;《中央軍委關於消滅白水曲靖等地敵軍的指示》,1935年4月25日;《中央軍委關於我軍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蘇區的指示》,1935年4月29日。這表明,他們當時並沒有向西北部邊界地區發展的打算。
根據有記載可查的歷史文獻,中共最早提出接通與蘇聯的聯繫,是在1935年的5月份。當時,紅軍在西南地區建立根據地的作戰屢屢受挫,而中共中央了解到,蘇聯通過援助盛世才,已在新疆形成了自己的重要影響。因此,毛澤東等人認為應當向北發展,用周恩來在兩河口會議上的話來說,就是:當時中央的「決定是到岷江東岸,在這地區派支隊到新疆」《周恩來關於目前戰略方針的報告》,1935年6月26日。
6月中旬,紅軍一、四方面軍在川西匯合,實力增強,中共中央於是進一步提出了「佔領川陝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的戰略設想,這一設想仍舊包含著準備與蘇聯接通的意圖在內。關於這一點,從朱德等人6月16日給四方面軍負責人張國燾的電報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電報明確提出:準備「適當時期以一部組織遠征軍,佔領新疆」,打通國際路線。《朱毛周張為建立以川陝甘三省蘇維埃政權問題給張徐陳等電》,1935年6月16日。出乎意料的是,張國燾對此卻頗表懷疑。
6月17日,張國燾致電中共中央,說川北地區地形不利,給養又斷,我軍意圖已為敵悉,目前不宜再過岷江東進和北上,而應迅速西進經阿壩進入甘、青或南出雅安、名山、邛崍、大邑地區。無論是向西進入少數民族地區,還是向南與川軍爭地盤,以往數月的作戰都證明困難太大。故6月18日和20日,中共中央接連兩電錶示不同意張國燾的主張,並建議張國燾來中共中央所在地懋功「商決一切」參見《毛澤東年譜》(上),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459—460頁。。兩河口會議就是這麼來的。
關於兩河口會議,除了前面提到的張國燾的回憶聲稱中央的計劃受到激烈批評以外,過去的一些黨史著作也用了不少筆墨來說明張國燾是如何反對中央北上計劃的。事實上,至少我們從會議記錄上是看不到這種情況的。由於會前做過工作,張國燾在會上表現得十分隨和圓通。他承認:目前向西去阿壩要通過草原地區,夏天雨季長途行軍會有很大的減員;向南往成都打雖不成問題,但敵人會很容易調集兵力,故「發展條件是甘南與我有利」,「政(治)局應決定在甘南建立根據地,至於怎樣打,軍委應做具體計劃」,「政局應趕快決定迅速的定下」。《張國燾在兩河口會議上的發言》,1935年6月16日。因此,會議決定「全體通過恩來的戰略方針」,並迅速弄好具體計劃。兩天後,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先後擬定了《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戰略方針的決定》、《關於向松潘前進的部署》和《關於松潘戰役計劃》,各部隊由此開始了具體的北上作戰行動。參見《毛澤東年譜》(上),第461—462頁。
毛澤東說:地理上靠近蘇聯,軍事上飛機大炮,意義重大
兩河口會議沒有具體提出接通蘇聯的問題,但其北上方針明顯地包含著力圖把甘肅西部乃至新疆「控制在我手裡,背靠西北」,退可依託蘇聯,進可逐鹿中原的戰略設想。只是,對於許多人來說,這個時候要想實現這一設想純粹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
蘇聯軍事顧問李德就明確認為,這樣做一來會給蘇聯造成麻煩,以至危及蘇聯的安全,二來以現有實力也很難實現。更多的領導人則顧慮到鮑羅庭以往所犯的「逃跑主義」錯誤,擔心「打通國際路線」的設想有退卻畏縮之嫌,因而極力強調北上計劃「不是打通蘇聯,而是向前」,是進攻。張國燾考慮得更多。他根據四方面軍過去的作戰經驗,對打地方軍閥的部隊比較有信心,對打國民黨的中央軍則顧慮重重。當他得知北上要遇上蔣介石的嫡系部隊胡宗南部后,立即對北上方針猶豫起來。與此同時,這個時候四方面軍無論人還是槍的數量都幾倍于中央紅軍,張國燾相信有必要先解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陳昌浩據此於16、18日兩電中央,要求「請燾(指張國燾——引者注)任軍委主席,朱德任前敵指揮,周副主席兼參謀長」,由「軍委獨斷決行」以利集中。因此,張國燾雖然同意了兩河口會議的決定,很快卻開始拖延部隊的行動了。
還在7月10日,一方面軍進至岷江西岸的毛兒蓋地區,開始逼近松潘,四方面軍主力卻遲遲不進。一旦被敵人識破紅軍北上意圖,胡宗南部主力大批趕到阻截,整個計劃均將告吹。故朱德、毛澤東等已不得不急電張國燾,稱:「分路迅速北上原則,早經確定,后勿(忽)延遲致無後續部隊跟進,切盼……各部真能速進,勿再延遲坐令敵佔先機。」《朱毛周關於四方面軍北上致張電》,1935年7月10日。
眼看不滿足張國燾等人的要求難以確實北上,經這時在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提議,中共中央於7月18日決定在軍委設總司令及總政治委員職,由張國燾任總政治委員,為軍委總負責者,並由四方面軍司令員和政治委員徐向前、陳昌浩兼前敵部隊指揮和政委。《中央軍委關於朱德總仍兼紅軍總司令張國燾為總政委通知》,1935年7月18日;《朱張周王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組織前敵指揮部決定》,1935年7月21日,見《毛澤東年譜》(上),第463頁。至此,張國燾才又開始指揮四方面軍與中央紅軍協調行動,實行北上進攻松潘計劃。但隨即又出現各部隊嚴重缺糧的情況,原定7月28日各部隊到達預定位置的計劃再度被延誤。很快,胡宗南軍主力趕到松潘地區,奪取松潘的戰役計劃被迫取消。
既然北上必與國民黨中央軍遭遇,張國燾再度對是否繼續北上發生動搖。而這個時候,四方面軍與一方面軍之間的團結也接連出現問題,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開會統一思想。
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附近的沙窩再度舉行會議,討論由張聞天提出的《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形勢與任務的報告》,報告進一步重申了兩河口會議所作的北上決定的必要性,並直截了當地強調了爭取西北地區,背靠蘇聯的意義。
毛澤東在會議上作了重要發言,也集中提出了背靠蘇聯的問題。他解釋說,西北地區是「統治階級最薄弱的一環」,是「帝國主義勢力最弱的地方」,然後特彆強調了「蘇聯在這地區影響大」的問題。他說:
地理上靠近蘇聯,政治上物質上能得到幫助,軍事上飛機大炮,對我國內戰爭有很大意義。五次圍剿開始堡壘主義,我們對技術方面應很大的作準備。……我們基本上靠自己,但(應)得到國際的幫助。……因此要用全力達到戰略方針,首先是甘肅這區域,但要派支隊到新疆,造飛機場、修兵工廠。《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35年8月6日。《毛澤東年譜》(上)未收錄這方面的發言內容。見《毛澤東年譜》(上),第465—466頁。
對張聞天、毛澤東的主張,張國燾和四方面軍領導人如陳昌浩、傅鍾等雖未直接反對,但話里話外卻明顯地表示出不那麼贊成。
比如說什麼不管蘇聯援助我們的態度如何,我們共黨應把責任放在自己身上,不要以為與蘇聯接近就是要從蘇聯得到技術幫助;說什麼同志們對西北方向講了很多,但不要把少數民族問題看成是一個困難;說什麼從西北發展到東南是可能的,但政治局決定整個革命問題不能偏向一邊,不應限於一種因素,如此等等。
很顯然,張國燾等人對北上方針實際上是不同意的,但他們在政治局中不佔多數,一時又找不出十分充足的理由加以反對,因此說起話來只好含糊其辭。結果,會議仍舊通過了張聞天的報告。20日,政治局又在毛兒蓋開會,按照毛澤東的提議,制定了《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進一步規定了北上戰役行動的具體步驟。只是,既然張國燾等人內心不贊成北上,其領導下的四方面軍人多槍多,張在名義上又是軍委總負責者,部隊調動指揮及其具體軍事行動仍不免受到嚴重掣肘。
8月底,中共中央所在的右路軍力克包座,打通了北上甘南的通道,張國燾面臨嚴峻選擇。終於,張國燾以缺糧和葛曲河水大不能徒涉等理由,於9月3日下令左路軍離開北上路線,西進阿壩地區,不走了。形勢一時間變得異常微妙和複雜。
紅軍分裂,毛澤東提議:經過游擊戰爭打到蘇聯邊界去
9月8日,張國燾避開中央,下令正在右路軍的前敵總指揮徐向前、陳昌浩率右路軍回頭南返。此一命令引起中共中央高度警覺,一、四方面軍迅速面臨分裂危險。
關於一、四方面軍的分裂,各種書講得很多。始終成為懸案的,是毛澤東提到過的那封張國燾想要「武力解決」一方面軍的「密電」。實際上,即使沒有所謂「密令」,以當時情勢和以後紅軍發展的歷史事實,中共中央不顧一切單獨北上也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接獲張國燾電令后,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王稼祥以及徐向前、陳昌浩當晚即在周恩來的住處開會。經勸說,徐、陳均同意北上更為有利。於是當晚七人聯名電張,說明無論地形、經濟還是居民環境,阿壩都不是久留之地。北上再困難、減員再嚴重,只要進入甘南,就補充有望。甘南若不能住,「即以往青寧新說,亦遠勝西康地區」。
但9日張國燾再電陳、徐並中央,堅持原令,強調川敵好打。結果,陳昌浩改變了態度,準備執行南下命令。經勸說無效,不得已,毛澤東等當晚緊急開會討論對策。關於要不要單獨北上的問題,討論中一些與會者曾經有過顧慮,擔心這不符合布爾什維克的原則。但在毛澤東詳細分析了事態可能的發展趨勢后,大家都贊同了毛澤東的提議,以周恩來任右路軍指揮,密令一方面軍主力連夜北上。關於中共中央決定獨自率領一方面軍主力脫離四方面軍緊急北上的原因,有各種不同的說法,但較為流行的是多數中共黨史書上關於張國燾密令陳昌浩等以武力脅迫中共中央南下,被葉劍英發覺報告毛澤東,毛迅即決心採取此一行動的說法。但考慮到9月10日後中共中央與張國燾來往電報一度十分頻繁,雙方各陳己見,說明原因,卻均未提到密電一事。爾後中共中央召開的討論這一事件專門會議也絲毫未提及此一密電,故筆者對上述說法表示懷疑。參見《中央致國燾同志電》,1935年9月10日;《中央政治局指令——給陳昌浩、徐向前同志》,1935年9月10日;《中共中央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1935年9月10日;《中央致國燾同志電》,1935年9月11日。參見《毛澤東年譜》(上),第471頁。
在脫離右路軍陳昌浩指揮下的四方面軍部隊之後,中央致電張國燾,稱「閱致徐、陳調右路軍南下電令,中央認為完全不適宜的。中央現在懇切地指出,目前方針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左路軍應速即北上,在東出不利時,可以西渡黃河,佔領甘、青、寧、新地區,再行向東發展。」同日,毛澤東等以政治局名義命令陳昌浩、徐向前說:「八日朱張電令你們南下,顯系違背中央累次之決定及電文,中央已另電朱張取消該電。」「為不失時機的實現自己的戰略方針,中央已令一方面軍主力向羅達、拉界前進。四、三十軍歸你們指揮,應于日內尾一、三軍后前進,有策應一、三軍之任務。以後右路軍統歸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同志指揮之。」與此同時,中共中央還發布了《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參見《毛澤東年譜》(上),第471—472頁。
當然,中共中央擺脫張國燾四方面軍的掣肘,率一方面軍主力一、三兩個軍單獨北上,情形也並不樂觀。因為這時一、三兩個軍作戰部隊很少,全部加起來也不過4000餘人,重新編製后的部隊只有六個團的戰鬥部隊,而實際的兵力其實只是六個營。以這樣少的兵力,要想實現原定的北上在川陝甘或者在甘南建立根據地的設想,是很少可能性的。因此,向北打到蘇蒙邊界去的問題立即提了出來。儘管李德建議看個把月結果再定方針,不一定要到蒙古去,但在9月12日舉行的政治局會議上,與會者顯然都同意毛澤東所提出的行動方針,這就是:
目前應經過游擊戰爭打到蘇聯邊界去,這個方針是目前的基本方針。過去中央曾反對這個方針,(因為)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應該在陝甘川創造蘇區。但現在不同了,現在只有一方面軍主力——一、三軍,所以應該明白指出這個問題,經過游擊戰爭,打通國際聯繫,得到國際的指導與幫助,整頓休養兵力,擴大隊伍。……我們完全拒絕求人是不對的,我想是可以求人的,我們不是獨立的共黨,我們是國際的一個支部,我們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們可以首先在蘇聯邊界創造一個根據地,來向東發展。《毛澤東關於目前行動方針的報告與結論》,1935年9月12日。
在從最初撤出江西蘇區時的87000人銳減到幾千人之後,每一個中共中央和一方面軍的領導人都明白,現在這種形勢對於他們將意味著什麼。彭德懷估計:改編后的部隊,在進攻作戰中一個團只可以對付國民黨軍的一個營,這也就是說,對付國民黨軍,全部紅軍力量只能與其兩個團的兵力作戰。這自然「要謹慎,不能冒險」。正如毛澤東所說:國民黨軍隊可以調動的兵力有幾十個師,而紅軍再找不到可靠的根據地作為依託,就不得不永遠打游擊戰,以致成為瓮中之鱉,直至被打散。而如果能夠通過游擊戰爭打到蘇聯邊界去,就有可能保存這幾百名幹部和幾千名戰士,將來「更大規模更大力量打過來」。《毛澤東關於目前行動方針的報告與結論》,1935年9月12日。
然而,比較一年後數萬紅軍實施「打通國際路線」作戰而未得的情況來看,以這幾千兵力能否由川陝邊界一路打到外蒙古邊界上去,實屬不得已而為之的冒險計劃。這是因為,中央紅軍已輾轉跋涉西南各省,歷經艱難,人數銳減卻始終無法找到落腳點。靠剩下的這少數兵力,要想在西北更偏遠、荒蠻、更少革命基礎,甚至毫無地理、人口、物產知識的地區創立根據地,幾乎沒有可能。因此,北上蘇蒙邊界是保存紅軍和中共骨幹的唯一選擇。
但是,以中央紅軍當時所在的川甘邊界地區,要想打到蘇蒙邊界去,還有相當遙遠的路途和想象不到的種種困難。當時他們所知道的只有兩條路線。一是經甘肅、寧夏,直趨綏遠的定遠營,這是1920年代鄧小平等人由蘇聯前往馮玉祥國民軍工作時曾經走過的路線;一是經甘肅狹長的河西走廊前往新疆,這是避開國民黨中央軍追擊的一條迂迴路線。無論走哪條路線,幾千疲憊的紅軍部隊要想掩護數百徒手的中央幹部大隊人員安全到達目的地,仍舊危險重重。好在中共中央進入甘南不久就從拾到的一張《大公報》上了解到在陝北還存在著一塊蘇區,可以做紅軍的落腳點。於是,他們及時地改變了原定的方針,衝破敵人的圍追堵截,殺向甘北,然後轉入陝北落下腳來,不走了。
共產國際提出援助方案,斯大林贊成紅軍靠近蘇聯
選擇北上,以及「打通國際路線」的方針,在中共領導人當中,十分明顯地始終存在著某種顧慮。這不僅因為曾經歷史上有過鮑羅庭「逃跑主義」的陰影在作怪,而且因為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所受到的是「保衛蘇聯」的教育和熏陶,他們往往首先會考慮自己的做法是不是會給蘇聯帶來什麼不利的影響。因此,如果不是形勢所迫,他們通常是不會主動採取這一步驟的。但他們這時不了解的是,莫斯科此時其實並不反對他們向北靠攏,甚至有意向他們提供援助。
還在1930年,斯大林就噎開始意識到需要武裝援助中國紅軍的問題了。斯大林當時曾對中國紅軍及其根據地能否在靠近中國心臟地區和主要交通要道的南方各省長期堅持下去,表示悲觀。在幫助中共中央制定未來發展計劃的時候,他當著周恩來的面明確提出:將來紅軍如果能夠向西發展,得到四川那樣一塊地方就好辦了。因為四川具有進可攻退可守的極為有利的自然地理條件,又較為偏僻,紅軍不會因過分靠近南京受到國民黨軍隊頻繁的圍剿與進攻。參見拙作:《「立三路線」的形成及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和遠東局的爭論》,《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
最早按照斯大林的建議把紅軍開入四川的是張國燾。1930年斯大林向周恩來等中共代表提出向四川發展的建議時,張國燾恰好也在莫斯科。正是在他的帶領下,原來堅持在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區的紅四方面軍於1932年底向西退進了四川的北部地區。儘管張國燾此舉純粹是反圍剿戰爭失利的結果,但其西去的行動不僅沒有受到共產國際的批評,反而受到它的讚揚。共產國際執委會一知道紅四方面軍在川北建立起川陝根據地的消息,就立即發來電報,對紅四方面軍在戰爭不利時主動撤出原蘇區,退入四川的行動給予積極的評價。電報稱:「在保衛蘇維埃領土時,必須保持紅軍的機動性,不能以付出重大損失的代價把紅軍束縛在一個地方,這一點對於保衛中心地區尤為重要。」因此,「我們對四方面軍主力轉入四川的評價是肯定的。我們認為,在四川、陝南和有可能的話向新疆方向擴大蘇維埃根據地,具有很大意義」。《共產國際執委會致中共中央電》,1933年3月,轉見《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2期。
1933年3月共產國際執委會的這封電報,是目前所能見到的共產國際領導機關最早的一份明確建議中國紅軍向西和西北地區發展的正式的指示電。這封電報清楚地表明,蘇聯和共產國際希望紅軍西去川陝甘,並且希望紅軍接通新疆地區,儘可能地向接近蘇聯的方向發展。這一建議的目的,很顯然噎包含著蘇聯希望利用中國西北邊界向紅軍提供幫助的考慮在內了。
1933年秋天以後,由前中共陝甘游擊隊改組的紅二十六軍在陝甘邊界地區漸漸變得活躍起來,這種情況進一步引起共產國際方面的高度重視。共產國際領導人幾次要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提醒中共中央下大力氣發展這一地區的軍事工作和政治工作,以便打通川陝蘇區與新疆之間的聯繫。根據共產國際的建議,中共駐共產國際的正式代表王明和康生兩人曾兩次寫信提到這個問題。其1934年9月的一封信更把向西北發展的工作提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信稱:如果我們能夠將陝北與陝南的游擊運動發展起來,我們就能夠接通川陝蘇區與新疆的聯繫,從而接通蘇聯。因此,「我們提議,中央與四川、陝西的黨共同努力完成這個與中國革命有偉大意義的工作」。共產國際也已同意中共為此派遣一部分西北與北方的幹部立即去蘇聯學習,以便派去西北地區開展工作。《康生、王明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4年9月16日。
自1933年秋天以後,由於新疆新的統治者盛世才積極靠攏蘇聯,蘇聯迅速開始展開其對中國新疆的工作。至1933年12月和1934年1月蘇聯兵分兩路進入新疆幫助盛世才打敗甘肅馬仲英部與伊犁張培元部的兩面進攻,更進一步加強了蘇聯在新疆的影響力。這樣一來,中國紅軍由東向西發展,蘇聯的勢力則由西向東伸展,兩方面的距離迅速縮短,通過中國西北使中國紅軍接通蘇聯的前景對共產國際更具吸引力了。
1934年夏,共產國際駐上海的遠東局軍事代表弗雷德回到莫斯科。在和各方面負責人交談之後,他很快向共產國際副總書記兼聯絡局局長皮亞特尼茨基就中國紅軍的未來發展方向問題提交了他的建議書。在這份建議書中,弗雷德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中國紅軍向西北發展的戰略意義。
弗雷德在這一文件中明確提出,目前紅軍及蘇區在中國南方,包括在江西的發展都遇到了嚴重的困難,中國革命當前最具發展前途的根據地是在四川。但四川的工作還遠不能令人滿意,它在各方面的工作都相當薄弱,不能適應建立鞏固根據地的要求。特別重要的是,根據幾年來鬥爭的經驗,紅軍的發展極度需要來自國外的援助,而這種援助只能通過加強中共在西北的工作和紅軍向西北發展的戰略來實現。為此,弗雷德提議,立即在蘇聯中亞細亞的阿拉木圖組織由中共軍政領導人和共產國際聯絡部人員聯合組成的中共西北局,開始調查通過新疆、外蒙等地派遣人員到中國西北各省發展游擊戰爭的可能性,直接援助陝北的紅二、六軍,並通過他們接通四川紅軍。為此不僅應當從莫斯科派遣一些有能力的和具有主動工作精神的中國幹部到中國西北地區去,而且應當考慮派遣一些在蘇聯遠東地區工作的華人幹部,包括一些從東北來的游擊隊成員,通過新疆到中國的西北地區去,充分利用西北地區的各種武裝力量,並把它們改造成革命的武裝,使之與四川的鬥爭匯合起來。同時還應考慮在蘇聯的中亞細亞地區組織一個秘密的軍政學校,包括建立一個至少足夠裝備五萬人的秘密武器庫。特別是對於軍事援助這一點,弗雷德具體解釋說:「可以肯定,僅僅培養幹部是不夠的,我們將來必須要為紅軍提供武器,包括飛機大炮等等。為此我們應該從俄羅斯向中亞細亞運送足夠裝備五萬人的武器裝備,並在那裡建立武器庫」,以便隨時可以根據需要向西北地區的紅軍提供軍事上的幫助。《弗雷德的建議》,1934年9月16日;《皮亞特尼茨基給皮爾金同志的信》,1934年11月3日,原檔存莫斯科俄羅斯當代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以下稱中心檔案),檔號495/19/575。
就在弗雷德的建議書提交上去后不久,共產國際即開始委託紅軍情報部門著手對中國西北地區進行具體的調查工作。因此,1935年產生了一些重要的調查報告,如《關於中國西北邊疆情況的報告》,和《關於內蒙古一般情況的報告》等。這些報告說明,從中國西北地區接通蘇聯至少有兩條道路可供選擇,一條是經過新疆的哈密進入甘肅西部地區,一條是經過外蒙進至綏遠的定遠營,接通寧夏和山西。後者要比前者對紅軍更為方便,但暴露的可能性也大得多;前者距離較遠,道路困難,費時較長,但由於新疆掌握在盛世才的手中,保密性卻好得多。《關於中國西北邊疆情況的報告》,1935年;《關於內蒙古一般情況的報告》,1935年,中心檔案,檔號495/19/575。
從1935年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關於紅軍行動的一份報告來看,共產國際在這一年的4月間噎決定要紅軍在靠近蘇聯和外蒙的西北地區創立戰略根據地了。該報告宣稱:「現在,不僅四川地區的西北邊界噎不存在任何嚴重的威脅,而且今後紅軍向陝西、甘肅方向發展具有非常遠大的前景,因為這些地方的游擊隊噎建立起一些重要的根據地,並且建立起獨立的蘇維埃政權。」紅軍「向西北發展的道路事實上噎打通」。蘇聯國防部、蘇軍情報局和共產國際聯絡局三家甚至聯合組織了一個三人組,特別研究了中國紅軍未來在中國西北地區的發展計劃及其蘇聯方面的援助問題,這個小組的一份報告也肯定,紅軍在西北發展以及接受援助是可能的。《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關於中國紅軍前線的新形勢的報告》,1935年4月;《有關軍事問題的報告(絕密)》,1935年,中心檔案,檔號495/19/575。
由此不難看出,到了1935年,蘇聯方面關於支持中國紅軍向西北地區發展和直接援助中國紅軍的戰略設想,噎基本形成了。正是因為如此,還在1935年8月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召開期間,蘇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就急忙地找到中共代表團,要他們選派一位重要幹部秘密潛回中國西北地區,尋找正在北上的紅軍,一面轉達共產國際關於統一戰線的新政策,一面轉告中共中央努力向西北發展。斯大林特別叮囑說,告訴中共中央:
「紅軍主力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並不反對靠近蘇聯。」轉見《育英、聞天致朱德、國燾同志電》,1936年2月14日。
(待續)
原標題:蘇聯大規模援助中共紅軍的一次嘗試
文章來源:本文摘自《讀史求實》,楊奎松著,浙江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