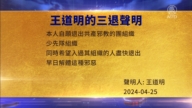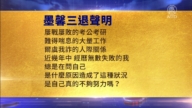(接上文)
十六
1997年7月2日,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那年7月1日中国收回对香港的主权,全国破例放一天假,2号才上班。一上班,一位同事就把一套书往我桌上一放,说:“给,《转法轮》!”
我一看,是大妹妹从绵阳寄来的包裹,包装已经破损,所以同事看见了书名。我从小就爱看书,大学和研究生时代,哲学、宗教、人体特异功能、气功、《周易》等等,几乎什么都研究过。一方面,我总相信宇宙能维持稳定和和谐,一定存在着某个终极真理,我想知道那个真理到底是什么;另一方面,我对人有了这条命到底应该拿来干什么,感到相当困惑。人难道就是应该为了活着而活着,追逐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然后一死了之吗?
许多时候,我找不着北。我不愿像周围许多人那样争争斗斗、溜须拍马,削尖脑袋往上爬,我觉得那样太累了,太有悖我的本性了。可我又不甘心由于我的不“奋斗”而落于人后,被人欺负,让人瞧不起。我不知应该遵从和坚守什么,许多时候很迷茫、很困惑。表面的成功和风光那是给别人看的,一点儿也解不了我心中的惑。
再加之,92年我分娩时因医疗事故造成大出血,又因输血染上医学上尚无药可治的丙型肝炎,从此人生陷入低谷和绝望中,在医院里一躺就是好多年。
97年初,虽然在经历了好几年的住院“生涯”后勉强开始上班,但也只是因为我不愿一辈子当疾病的奴隶。我因医疗事故而倒下时,才刚刚工作了一年多。人们常将女性比作鲜花,我感觉自己就像一朵还未来得及完全绽放的鲜花,却在疾病的摧残下一夜凋零。我不甘心让人生就此葬送在医院,想“假装”自己还正常,不管还剩多少时间,我都想让自己“正常”的活着。
话是这样说,可我自己知道,我活得比《红楼梦》里的林妹妹还累,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做错一件事,唯恐被疾病耻笑了去。我的身体实在太弱,一有点儿风吹草动、流行感冒之类的,我第一个就倒下。
因此,到97年7月,在经历那么多之后,我是以一种可有可无的心情打开《转法轮》的。可是,当我读到第四页中关于人的生命来源的阐述时,却突然被抓住了,从此我再无空闲对书中的内容做任何“裁判”。我迫不及待一口气读完了妹妹寄来的四本书,心中只有一次又一次的惊叹:“原来如此!!!”
可以说,《转法轮》带给我的冲击,比我之前读过的所有的书加起来还大。我所有关于人生和宇宙,甚至人类社会的疑问,都在书中得到了解答。我再也不困惑了,我知道自己来到世间的目地了。我当即决定修炼法轮功。
很快的,我了解到,原来大妹妹和母亲经朋友介绍,已经在一个多月前开始炼了,炼了一个月就觉得很好,所以赶快给我寄一套书来。

1998年,我在深圳一个公园里打坐。这是镇压前拍的唯一一张炼功照片。(作者提供)
十七
母亲和小妹妹是我上大学离开家后,才终于调到绵阳,与父亲和大妹妹团聚的。为了这次调动,母亲不得不放弃已从事近三十年的教师职业,和当时不算低的“教龄工资”,转而进入法院系统,原因是绵阳哪一个学校也不肯接收妈妈,说是没有人事编制。努力多年后,父亲所在司法系统总算开恩,答应内部“解决”,把母亲“安置”到绵阳市中级法院,由最低的书记员职位做起。
母亲可真是个女强人,她那时已四十多岁,为了家庭团聚,不但敢于从入门级开始从事一个新的职业,并且勇敢的与女儿一起上起了大学:我上的是正规的北大,她上的是函授的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母亲念的很努力,也很吃力。毕竟年龄大了记忆力不够好。不过,她成绩很好,几年后顺利毕业,既雪了年轻时因家庭出身未能上大学的“奇耻大辱”,职位也慢慢从书记员升到法官,直至审判长。
十八
97年时,六十四岁的父亲已退休,母亲和妹妹开始炼法轮功时,他不炼,也不信,但也跟她们去公园。她俩炼功,他去跳国标舞,算是锻炼。退休后,父亲就迷上了跳舞这种锻炼方式。有一天,他跳完舞,妹妹和母亲还没炼完功,他就站在一边等。等着等着,他自己说,他突然看见了(存在于另外空间的)法轮,足有游泳池那么大!
在这种“眼见为实”的景象的冲击下,父亲也开始非常投入的修炼法轮功,并时不时跟我们分享他的天目又看见什么了:比如他看见自己炼第三套功法,手臂上下运动时,有成串的小法轮跟着上下运动。他描述说,这个“成串”,就是旧时候用的铜钱那样穿成串的感觉。
父亲说起这些时,带着一种小孩子分享秘密时的天真和喜悦。我和妹妹交流说,也许是因为父亲天性中纯朴的一面未受污染,所以才会一修炼就开天目,就看到这么多超常的东西吧。
又过一段时间,父亲专门打电话来,告诉我他的老花眼好了!
他说,他现在虽然退休了,但还是被返聘回去办些案子。有一天他整理办公桌,看见许多碎纸片。他一边收拾一边想,哪个小孩这么淘气,把报纸剪的这么碎?
突然,他发现,自己居然看见了报缝里的小广告上的字!
这种报缝小广告的字体特别小,以前不戴老花镜,是绝对看不见的,而现在居然裸眼看见了?
他怕这只是一时的,所以没敢声张。
第二天,他对自己进行测试,看是不是不戴老花镜还能看见那么小的字。结果跟前一天是一样的。
他连续测试半个月,才敢确认老花眼确实好了,不需要老花镜了,这才高兴的打电话告诉我。
不过,他又特别补充道,因为修炼人讲究去除执著,不能生出欢喜心、显示心来,所以这事儿除了跟家人和炼功点上的辅导员私下讲过外,他并没有到处张扬。
十九
老花眼好了只是修炼后父亲身体变化的一个方面,其他的变化还很多,比如他的血压,以前一直很高,高压经常是200多,常年靠降压药维持,但还是经常出现险情。有一次他与母亲一起骑自行车出去,母亲在他后边,眼见他骑着骑着一头就栽倒在地——原来是血压太高引起的昏迷。当时把母亲吓坏了,从此再也不许他骑自行车。
修炼后,他的血压很快恢复正常,再也不用吃降压药。慢性咽炎、鼻窦炎等许多毛病也都好了。
98年夏,我带女儿从北京回四川探亲。见到父亲时,我大吃一惊:他看起来至少年轻了十岁!
在我记忆中,父亲从来没胖过,永远是骨瘦如柴的模样,脸上的皱纹因此很深。他谢顶也早,三十多岁头顶就开始秃,不到四十岁,就有小孩叫他“爷爷”,他一直以此自嘲。

93年10月,父亲六十岁生日照。头上的假发是我工作后给他买的礼物。他收到后一直戴着。(作者提供)
炼功后,他体重增加了十多斤,脸上的皱纹自然被“长平”许多,所以乍一看,就觉得他年轻了不止十岁。
再过两天,我发现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那就是他走路时的体态。哈代的名著《德伯家的苔丝》中有一个情节一直让我记忆犹新。书中的“坏蛋”,也就是奸污了女主人公苔丝的亚雷‧德伯在与苔丝分手近四年后,变身为一名牧师。有一次他正在布道,苔丝突然看见他,并十分惊讶于他的变化,而他显然还没有认出外貌和衣着已大改的她。她不想让他认出自己,想转身悄悄走开。
可是,她不走动还好,她一走路,他立刻从她的走路姿态中认了出来:这是苔丝!
从这个细节中,可以看出,一个人走路的姿态是非常特别的,甚至比他的外貌和衣着打扮更能代表他。
所以,当我看到修炼一年多后的父亲的走路姿态时,心中的讶异不亚于听他说自己的老花眼好了。他的步伐完全变了,不再像以前那样拖泥带水,暮气沉沉,而完全可以用“身轻如燕、步伐矫捷”来形容。
我能看出来,这种改变,是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唯有特别熟悉他的亲人,才能一眼看出来。而这种变化,又只有在生命很深的层次、深入到细胞以下的层次发生了质的改变时,才会发生。
二十
我还看见父亲在家中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两张照片,一张是他修炼前骨瘦如柴、老态龙钟的样子,一张是修炼后腰板笔直、面庞丰满的打坐的样子。两张照片旁,还有他手书的一首小诗,我记得最后一句是“再苦再难永向前”,表明他修炼的决心。他说,只要一有客人来,他必定让客人看这两张照片,说这是弘扬法轮大法的最佳材料。
我从未看见父亲那样开心过、骄傲过、话多过。在那一个夏天,父亲跟我说过的话,比他这一辈子中都要多。
二十一
可惜,好景不长,99年7月,对法轮功的镇压铺天盖地的开始,在我还没完全反应过来之前,就已身陷囹圄好几次。
跟我们住在一起的公公婆婆吓坏了,在多次劝我放弃修炼未果后,婆母想到我父母。她认为是我父母让我修炼的,因此只有他们才能让我放弃。她打电话跟他们沟通。我不知父母是怎样跟她说的,不过显然是没有如她所愿。婆母放下电话绝望的叫道:“我到四川去跟你父母拼命!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我一方面真怕她失去理智从北京跑到四川找我父母哭闹,一方面又痛彻心肺的想:“您要真的不想活了,为什么不去找江泽民拼命!”
婆婆退休前是个妇女干部,文革中也曾被揪到台上“坐飞机”、挨批斗,之后一家人不得不逃到乡下躲避。对中共残暴的深切体会化作她深深的恐惧和臣服。她很难原谅、也很难理解我为何不能够跟她一起恐惧、跟她一起接受“胳膊拧不过大腿”这个理。
二十二
99年秋,我听功友说,原法轮大法研究会几名成员就要被开庭审理了,他们的罪名之一是“煽动”1999年4月25日的万人上访。那天有超过一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信访办外集体请愿,我是其中一名。我想到法庭上去作证,说那天上访是我自己要去的,没有任何人煽动我。
父亲知道我的想法后告诉我,这是徒劳无益的。绵阳市司法局曾召集市里所有律师,传达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政策,主要内容有:
1、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不同于一般刑事犯,因此虽然一般的刑事犯可以由律师出面保释,但法轮功学员一律不得保释;
2、法轮功学员大方向就错了,因而在法庭上辩护时,不得像其它案件一样,去抠公诉人的什么证据充分不充分、事实确凿不确凿等“小问题”;
3、律师辩护状必须上交给有关领导审批,在法庭辩护时,只能照审批过的辩护状作书面辩护,不许说辩护状之外的话。
父亲的传达没有让我感到意外,但99年12月26号那天,我还是来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准备去旁听庭审。然而,街上早已布满警察,我与其他一千多名法轮功学员一样,连法院大门的影都没看见,就被抓起来了。
在被送到看守所前,我们曾问派出所片警:“你估计这次得关多少?”
片警答:“不知道,得等上面的精神。”
“等上面的精神”,这才是中共所谓法治的“精髓”。在狱中,曾有功友问我:“你父亲是四川省十大律师之一,为什么不让他给你做辩护?”
其实,不光我父亲是四川省十大律师之一,我母亲那时也已做到绵阳中级法院的审判长,大妹妹则是绵阳涪城区法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可是这些有什么用?镇压后,大妹妹因到北京上访,被开除公职、党籍,还上了公安部全国通缉的黑名单,父母则处于被软禁的境地,不但经常被找去谈话,在他们住处的楼下,还安排了专门的眼线,父母的进进出出,都有中共密探记录在案。

99年初,我与母亲的合影。可惜当时觉得一切都会是“天长地久”的,会永远都那样、永远都在那里,因此竟然没想到要跟父亲也合个影。那时绝对想不到,我从此再也没机会跟父亲合影了!(作者提供)
二十三
我于2000年4月第四次被捕,之后判了一年劳教,送到北京女子劳教所。无论是父亲“十大律师”的地位、他的“1+1永远等于2”理论,还是我的“北大才女”光环、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身份,都未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父亲让我学理时,一定以为学理科可以让我避免重蹈他的覆辙。哪知道“计划赶不上变化”,炼功修心,也居然招来大祸。
在劳教所的每一天,我都在目睹或亲历种种惨绝人寰的反人道、反人伦和反人类罪行,在空前惨烈的野蛮摧残、心灵交战和意志鏖战中,无数人无数次的被逼到彻底崩溃的边缘。
在这个邪恶程度甚至超过纳粹集中营的地方,每一天都是生与死的交战。在经历了九死一生的惨烈后(详情请见拙作《静水流深 》),我于2001年4月获释。为避免再次被抓到洗脑班,获释后我只在家待了五天,便踏上漫漫流亡之路。
这时,我了解到,遭通缉的大妹妹“潜伏”在成都一家小酒吧打工,因为不敢出示身份证、不能办理暂住证,已出过好几次“险情”。那个小酒吧不能再待下去。我决意帮她逃到更安全、更妥当的所在。
我坐火车来到成都。妹妹打工的小酒吧真是只有巴掌大,而且只有她一个服务员。她每天要忙到深更半夜,等所有客人离开后才能将桌椅挪开,勉强打个地铺睡在地上。
这样的状况,她当然无法“招待”我。我们只好找了个小旅馆住下。一年多没见,我们有太多的话讲,整谈了一个通宵,到天亮肚子饿了,想出去买点吃的,一出门就碰到一个人,他看到妹妹后脸色一变,扭头就走。
这人是妹妹十年前的同学,正在成都当警察,显然知道公安部悬赏三万元通缉妹妹之事。
我们马上退房离开。妹妹无处可去,只能再回小酒吧,我则决定“潜回”距成都两百多里的绵阳,一来探望父母,二来从那里帮妹妹联系个去处。在当时的情形下,敢于接纳“通缉犯”的人不多。我只能在之前认识的功友中“搜寻”。
二十四
见到分开才一年多的父母,我像98年夏见到父亲时一样吃惊。只不过,这一次的吃惊是“反方向”的,不是惊喜,而是既惊且痛。
父亲再次变成瘦骨嶙峋、沉默无言的老人。比外表的变化更可怕的是,透过他黯淡无光的脸,我看见他的灵魂已萎缩成一小团,像风干的桔子皮一样,没有了任何生命力。一年多前那个神采飞扬,到处骄傲的说“我们家五口人,四口都炼法轮功”的父亲,再也看不到了。
中共来势凶猛的镇压把他吓坏了。他已停止修炼,不再与我讨论任何有关修炼的事,甚至也没问过一句我在看守所和劳教所的遭遇。也许是他不敢问,也许是他没兴趣问。对于一个灵魂已被风干的老人,这两者间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只听他喃喃的念过一句:“我已是快七十的人了,经不起折腾。把我的房子没收了怎么办?不给我发退休工资了怎么办?”
母亲的两鬓,则增添了许多不曾有过的白发。以前跟人说起她的三个有才有貌有出息的女儿们,母亲的声调总会立刻提高八度,要多自豪有多自豪。现如今,两个女儿成了党的敌人,随时会沦为阶下囚。母亲的自豪劲儿,再也提不起来,她也像是被霜打过一样,整日都蔫蔫的。
二十五
由于我和妹妹的特殊处境,彼此联络非常不方便。我当然不敢用家中的电话或手机直接联系她,那样立刻会为她招来杀身之祸。我只能用公用电话打她的传呼机,然后站在原地死等回话。她接到传呼后只能在可以从小酒吧中抽身时,找不同的公用电话回打给我。
克服了种种困难,我数日后终于找到可以投奔的去处。我跟妹妹约好,让她从成都起点站帮我也买好火车票,这样才能有座位,等火车到绵阳站停靠时,我用站台票上车跟她会合,一起北上逃走。
到了预定离开那晚,我如约到了绵阳站,妹妹却没有像说好的那样下车接我。
我感到不妙,还是硬着头皮用站台票上了车,找到原本应该是我俩的座位,却发现那里坐着两个看起来像是农民工的人。我向他们打听上车时有无见到一个长得如此这般的人,他们惊慌失措的一口咬定:没看见,我们一开始就坐在这里的!显然他们怕我说这两个座位不是他们的,跟他们抢座位。
我不得要领,只能在拥挤的火车上挤来挤去,从车头挤到车尾,来来回回找了一个多小时,直到火车开到一百多里外的下一站,还是不见妹妹的踪影。
万般无奈中,我只好补张票下车。这时已是凌晨三点,陌生的城市一片漆黑,下着滂沱大雨。我无处可去,无计可施,心比铅还要沉。
我不甘心一人离开,又打出租车回到父母家。没有妹妹的确切消息,我往哪里去?
一进门,就见地上扔着好多行李,母亲散乱着头发正在整理。
她看见我,也没问我为何回来了,只呆呆的说:“你妹妹昨天被抓了,这是她的行李,你妹夫刚从拘留所取回来的。这是在她身上搜出来的东西的单据。”
单据上赫然写着:法轮功书籍若干本、去太原火车票两张、火车站行李寄存票一张,等等。
我看着满地的行李,拿着那张单据呆在当地,大脑停止了思维。父亲一把拎起我的包,强行将我推出门外,奋力吼道:“快走!别等警察问出准备与她同行的是谁!”
我愣了一愣,望了望母亲斑白的两鬓、干枯的双眼,和一年多来不知衰老了多少的脸,咬咬牙转身走了。
二十六
后来得知,果然是那天我和妹妹在小旅馆迎面碰到的那个警察同学为了三万元悬赏金出卖了她。他向公安报告后,成都、绵阳两地警察联手,我这边在绵阳帮妹妹联系去处,他们那边一连数日在成都展开地毯式搜查。妹妹准备离开那天,已从酒吧辞了工。她先把行李寄存在火车站,因离火车出发还有几个小时,就想去跟之前一直不敢见面的几名同学朋友告别,并讲法轮功真相。哪知功亏一篑,在公共汽车上被抓住了。
在公共汽车上抓住妹妹这个细节,是母亲在绵阳《法制报》上看到的。警察抓住“要犯”,当作好大一件事,写了长篇报导,在报纸上邀功。
我很难想像警察们在常住人口多达一千多万的成都,到底动用了多少人力,才能在妹妹临时起意、随机乘坐的某辆公共汽车上,准确的将她“定位”。
二十七
几天后,我孤身逃到太原,接应我的人按原计划带我去了五台山。我站在山顶,想着本应站在我身旁的妹妹,看着满山遍野“人杂叫卖鞭炮鸣”(1)的与佛国世界的庄严毫不相干的“热闹”景象,听着出售纪念品的商店里的录音机放出的诵经声,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悲怆,突然充斥在胸,逼得我珠泪滚滚而下。神佛的殿堂和圣典被人用来做了无数次的金钱交易,而真正修行之人却在茫茫天地间找不到栖身之地。
不过,当我为妹妹落入魔掌而心痛之时,却永远不曾想到,父亲将我推出家门的那一刻,竟会成为我们的永诀。(未完待续)
(两亿人“三退”全球有奖征文大赛公告
http://www.epochtimes.com/gb/15/4/29/n4422842.htm)
文章来源: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