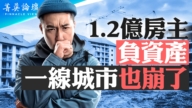【新唐人2013年6月7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上篇:对反右派运动的哲学思考
首先我们要来一个正名:你要是谈话,或写一般的文章,可以说“反右”或说“反右斗争”,但如果你写学术论文,因为它是科学研究,概念就要求准确无误。“反右”可指“反右倾”;“反右斗争”可指思想斗争,可指和风细雨的整风学习;而“反右派运动”是特指一九五七年那场针对知识分子的、席卷全国的、狂风暴雨般的政治大迫害运动。先作此规范,虽本书在以后论述中可能也有简便用法,但理解上只有做“反右派运动”一解,才可以免除歧义。
毛泽东说,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他对马克思主义,“只取它四个字,‘阶级斗争’”。他一生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始于“其乐无穷”,终于“不亦乐乎”。而把斗争胡诌成哲学的、最基本的是两篇:《实践论》和《矛盾论》。前者是斗争的认识论原理,后者是斗争的方法论原理。而“斗争”最广泛、最经常的实践形式,就是搞运动。行业的、地区的、全国的运动,接连不断。有许多时候是这个运动尚未结束,下一个运动已成不速之客,比如农村的四清运动尚未扫尾,文化大革命如迅雷不及掩耳,风吹树、风满楼、风起云涌、蜂拥而至,弄得有些拔腿较慢的四清工作队都出不了村。总之,正如农民对“运动”的描述:“这儿运动,那儿运动,全国规模的大运动。大运动,小运动,运动里头套运动”。“先整党,后整团,然后再整老社员。”“马头接马尾,马嘴咬马腿,运动不断头,赛过洪水和猛兽。”运动就成为斗争哲学的展开式,同时也成为毛泽东本质的展开式,“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本书就是通过对诸运动之一的反右派运动的哲学思考。透过复杂纷纭的乱象,特别是毛共散布的云遮雾罩,揭示出毛共极权是如何采用“恐怖”与“谎言”两手都要硬,以运动治国,来统治全国人民,特别是对知识分子进行灵魂消灭和肉体迫害(也包括消灭)的。
事后,邓小平总结反右历史教训,一曰:“正确的、必要的”,二曰:“扩大化”。别人较真,说:“难道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划错了还叫‘正确的’和只是‘扩大化’吗?”有好多单位全都改正了,一个没留,例如:“一九五七年的北京大学师生之中竟有一千五百人因‘反右扩大化’而蒙冤罗难,终于被开除公职或学籍,发配于穷山恶水、荒原大漠之间亡命了之,二十二年后,又把这‘扩大化’了的一千五百人无一例外地平反,此就北大来说:‘扩大化’已‘扩大’到无一正确全盘错误的程度!”(张元勋《北大一九五七》,明报出版社,页二)
邓小平、共产党给鼎鼎大名的北大数学系师生出了一道数学难题:“贵校到底‘扩大’了几倍呢?”(哪怕能算出个天文数字也行,甚至只要能由十个阿拉伯数字元号组成个任意什么数都行。)岂不知,共产党斗争哲学的精髓就在这里,叫做:“扩大化因为是必要的,所以就是正确的。至于什么叫做‘扩大化’,则完全不必在意。”你只用想想看,共产党搞的所有运动,为了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无论党内的,还是党外的,有一次不是“扩大化(包括无中生有)”的吗?是整肃AB团,还是延安整风?还是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胡风、肃反……?至于具体到这次反右派运动,你问为什么要扩大化呢?因为只有如此才能达到一箭三雕之目的:一是以言治罪,消灭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二是邓小平说的打击的人数太多,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当然他这是假惺惺。他手上沾满了知识分子的鲜血!包括后来镇压北京天安门“八九民运”。)
因为当时,惟其如此,全国才能处处都有黥面的反面教员,让人人恐惧填膺,个个心里住进公安局派出所;自然的结果,便是三,先说党内:有识之士,免开尊口,“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再说党外:全国的工人罢工、农民退社、学生闹事,所有“人民内部矛盾”,都乖乖地自动化解。事实证明,毛主席运用斗争哲学来运动群众,已达到出神入化之境界,论述斗争哲学则是夫子不言、言必中;果然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众口一词,一起大声高唱《社会主义好》!歌声传遍大江南北,听啊!它是多么地豪迈、嘹亮、激越,声情并茂!我要指出歌词中的两句:一句是“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建设高潮。”另一句是“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就是反右的辉煌战果。
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有如不尽长江滚滚来!反右胜利的政治之花,结出了大跃进农业卫星上天、钢铁元帅升帐的丰硕的经济之果,创造了人类史上让人目瞪口呆的奇迹。人民群众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泽东最完美地体现了他在《实践论》中提出的真理标准:“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他预想的目的达到了。往下的实践,是历史的下一章,请参阅我发表于《观察》网上的文章《大跃进的发生是反右运动的第一个恶果——对大跃进政治本质思考之一》;在《观察》连载至“之七”:《毛发动大跃进目的何在》。“之八”是:《大跃进是人类史上最大的人权灾难》,载于《民主中国》。
甲:思索
一“两类矛盾”说,非治国之正道
整个来说,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重在“处理”,是一篇指导实践——具体说,是对反右派运动量体裁衣、从发动到处理的文章。从“处理”着眼,它是一篇歪门邪道、祸国殃民的东西。它的理论基础是《矛盾论》,正如我在《〈矛盾论〉与论矛盾》一文中指出的那样,从“理论”着眼,它的概念混淆、原理荒谬、论点站不住脚。这是我通过一甲子的切身体验、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作出的一项严肃负责的、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科学判断。谓予不信,容我慢慢论证如下 :
【一】为什么说是“概念混淆”?
《正处》提出的的第一个问题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它是本篇的灵魂,其中提到“矛盾”这一概念的地方有九十九处。所以不能说它是“概念混淆,矛盾百出”,用数学的准确性来说是“矛盾九十九出”。
(一)从定义出发,明确“矛盾”这一概念
《辞海》上的解释是:(一)《韩非•难一》:“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莫之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后以“矛盾”连举比喻互相抵触,互不相容。如:自相矛盾。(二)辩证法的基本范畴。指事物内部所包含的既对立又统一、既互相排斥又互相依存的关系。(三)形式逻辑上指两个概念互相否定或两个判断不能同真也不能同假的关系。从作为辩证法的基本范畴来说,矛盾的内涵有二:一曰:内部性(自相矛盾);二曰:二重性(既……又……)。凡不具备这两条内涵者,就都不可称之为“矛盾”。
(二)“敌我矛盾”不具此内涵,故非“矛盾”,实际是“对抗”
矛盾是一个表达“我——我”关系的概念,即“自相矛盾”。但“我”的外延是可以扩展的:我——我们——我们国家、民族、人类社会等等。“敌——我”不属于矛盾的范畴,一则,它不具有内部性,即便在空间上距离很近,但从概念上讲,“敌”必在“我”外;二则,它不具有二重性,因为只有敌我对立、敌对、对抗、冲突、分裂、斗争、仇恨、拼杀……你总不能说敌我同一、统一、友好、亲密、团结、合作……如果既有前者又有后者,那就不是敌我了,就是化敌为友了。总之,只要是敌,就只能是前者。而所谓“矛盾”,必须是“既是前者,又是后者——具有二重性。”毛泽东在后来也是这样说的:“像托洛斯基那种人,像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还有像希特勒、蒋介石、沙皇,也都是无可救药,只能打倒,因为他们对于我们说来,是绝对地互相排斥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没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毛泽东选集》五卷,页四九七)这和我曾经例举的“人与草有矛盾”,因为田地里的草必须消灭才能保苗;而草地上的草又必须保留,以防土地沙漠化。但不能说“人与蚊子有矛盾”:蚊子只能消灭,不能既消灭又保留——因为不具二重性,所以不能说成是“人与蚊子有矛盾”。原来,矛盾“在本来的意义上来说”是具有两重性的,但毛所妄指的这个所谓“敌我矛盾”,却自己承认:“是绝对地互相排斥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没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既然只有一重性,所以就构不成矛盾。反过来说,在确认“敌我矛盾”就根本不是矛盾的前提情况下,把它确认为“对抗”,这时再来说“一重性”才是能够站得住脚的。如果你既承认敌我矛盾是“矛盾”,又说“没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这不成了悖论吗?在这里,又一次确证毛在《矛盾论》中引用的列宁所说的“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命题。由此“株连”,所谓“对抗性矛盾”,自然属于错误的概念,而成为伪命题。
这里还有个“人民和敌人”区分的标准问题。毛泽东是这样界定的:“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看来区分敌我的标准就是看他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可是,直到一九八零年代末,共产党自己也说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所以邓小平才有必要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的标准:“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页三七二)邓要判定社会主义,却在表述中用了“社会主义”这一未经定义的概念。他这个标准是不合逻辑的。所以直到今天,人们在谈论社会主义的时候仍是各说各话。令人感喟万端的是,多少人在“一念”(一个概念:反社会主义)之差中人头落地,更别说从黑五类直到臭老九、敌人人数之众了!其实,只用举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竟“选举”了一个敌人当国家元首,中共无产阶级司令部副统帅(上了党章、宪法的正统帅接班人)也都是敌人、都属敌我矛盾,就足以说明“两类矛盾”的说法,荒谬到何种可笑的程度、为害到何种可悲的程度!
(三)对矛盾概念切戒乱用
当毛说“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从此凡引自《正处》的话,便不再注明出处)的时候,他对矛盾概念的理解是正确的;当他说“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的时候,他对矛盾概念的理解就发生了混乱。这一句话中用了前后两个、含义各不相同的“矛盾”,前一个是对的,错误发生在后一个是用“矛盾”偷换了“对立”的概念,即“矛盾=对立”。正确的应该是“矛盾= 既对立又统一”。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前已说明,“敌我之间”不是矛盾,“对抗”也与矛盾断然不同。
“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这样的叙述,就篡改了矛盾概念的本意,本意应该是既一致又不一致。这里却成了“矛盾=不一致”。如用“不一致”代替“矛盾”,改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不一致。”虽然说法很别扭,但意思却没有错。而敌我之间要硬称为“矛盾”的话,就应该表述出二重性:“敌我矛盾是在利益根本不一致基础上的一致。”这样说可就不仅别扭,而且荒谬可笑了。原因无他,矛盾皆内部也。敌我不能捆绑成“夫妻”(这里的“夫妻”是作为典型的内部矛盾的范例)。
“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里的概念错误,是“矛盾=利益抵触”。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这里的问题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是否原于生产关系的“不完善的方面”;如果“完善”了是否就会没有了矛盾?
总之,我们在毛的论述中发现,矛盾概念歧义丛生。这一点,我在《〈矛盾论〉与论“矛盾”(上)》中,已分别列举出把“矛盾”等同于单纯的“对立”、“斗争”、“分裂”、“磨擦”、“离间”……等等的例子。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