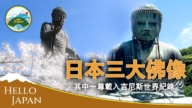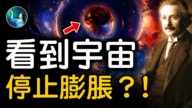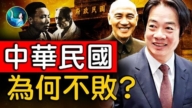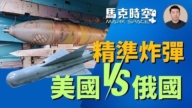【新唐人2012年3月1日讯】 【《谁是新中国》题解】 谁是新中国?谁才是真正的新中国?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后,又会出现长期的内乱和内忧?虽然能够一再地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统一了中国,捍卫了共和国统,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却又惨败在1945—1949的内战之中。嗣后,竟能够在台湾完成向民主的全面过渡,使孙中山先生民主建国的理想得以实现…… 如果是后者,为何又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全面复辟专制制度,虽然迄无外患,更无内忧,却造成“冤狱遍中华”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悲惨局面,为漫长的中国专制制度,补上了中世欧洲“教政合一”式极权专制统治的血腥一课。待到风雨飘摇之时,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开放”,然而,其成就虽不能与清政府相提并论,其命运却与清王朝一样而不能免,其腐败和腐烂,更为中国五千年历史所未有……
(接上期)
第四 马克思鼓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错误 社会根基和历史本质
一 错误的剩余价值观
应该说,十七至十九世纪的欧洲,在政治上,正处于民主革命日渐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复辟的新时代;在经济上,自由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亦使得欧洲的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但是,仍处在反复较量中的崭新民主制度或民主政体,还远未走向被确认和确立的历史阶段;自由主义的经济形态在其形成和发展中,非但来不及将历史所遗留下来的种种社会问题,诸如贫穷、愚昧等等,加以解决,而且,其自身在发展中所必然要出现的种种新问题,又日渐成为国家、社会、人民、尤其是思想理论界所注意的焦点。于是,较早获得发展的英国便产生了当代的政治经济学。因为,正是这个政治经济学,才真正是英国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发生和发展时期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者们之所以要称它为“古典的”,无非是要为自己留下一个“现代的和批判的”地盘而已。
然而,自十七至十九世纪,虽然是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发生和发展的新时代,却也是所谓社会主义思想 —— 即一切空想的和自称科学的社会主义,试图从传统农业社会的废墟上重新站立起来的“新时期”。其时,在思想上,既产生过英国的罗伯特·欧文和他的“共产主义新村”、即“新和谐村实验”,【注十六】又出现了法国的圣·西门与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在经济领域,尤其是在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虽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又产生了对劳动价值的错误认识。一八一七年,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已主张“商品的交换价值完全出于生产该产品所花费的劳动”。【注十七】一八二五年,海军军官托马斯·霍治司金又发表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的答辩”,即“反对资本要求,而为劳方辩护”。该辩护认为:如果象李嘉图所主张的那样,全部劳动价值都是劳动所赋予的,则全部报酬都应归劳动者所得;眼下,地主和资本家所得到的那一份必定是纯粹的榨取物。
托马斯·霍治司金企图用李嘉图极端偏颇的“劳动价值论”,来为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服务。同时代的英国哲学家詹姆士·穆勒,不仅指斥霍治司金的辩护乃是一种“疯狂的胡说”,而且,还在他批评哲学上的激进主义者、即企图为社会主义学说铺平道路的那些人时,【注十八】又说道:“这种见解假使传播开去,会使文明社会覆灭,比匈奴人和鞑靼人排山倒海的泛滥还坏”。【注十九】
二 马克思发展并异化了错误的剩余价值理论
不幸的是,这种见解不仅被传播开去,而且还作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克思正是从英国少数经济学家所侈言的劳动价值论,及对剩余价值理论的错误猜想出发,不但建立了剩余价值的绝对理论,即只肯定工人体力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而排斥其它任何劳动价值,将除工人以外的每一个社会成员对于社会所已担负的劳动一笔勾销。更有甚者,则是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之“物与物”的关系中,挖掘到了“隐藏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中的“人与人”的关系。这个关系,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流着无产阶级的鲜血”。【注二十】
由是,马克思以资本家榨取了工人剩余劳动价值为理由,武断地宣称“不论资本主义的经济如何繁荣,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注二十一】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无疑就是劳动群众日益贫穷化的代名词。然后,马克思又从所谓“社会化大生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绝对矛盾”,即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劳动群众就越是贫困出发,反对社会化大生产,反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因为“生产力的提高,只能不可避免地加深社会的阶级矛盾”。所以,他才宣言要“消灭私有制”,提倡“公有制”,并宣称“夺取政权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注二十二】
李嘉图和霍治司京的错误剩余价值论,终于在马克思的手里被异化、并被发展成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关系的理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个阶级对立与对抗的理论,无产阶级必须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予以“永久性怀疑”,和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用暴力专政的手段建立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显而易见的是,正是李嘉图和霍治司京的荒谬剩余价值理论,才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发展和全部理论证明,奠定了错误的前提和基础。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家不仅来自荒谬理论,而且来自他自身对于这个荒谬理论进行了绝对继承和极端发展的“本相”,自然已经证明了其全部理论和全部理论证明的荒诞不经。
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以人与人的关系去代替物与物的关系,就必然要走向以政治斗争的原则去取代甚至取消经济发展规律的歧途。其结果,无非是既以政治代替了经济,又以政治消灭了经济。马克思无幸在他那个时代作成一个共产专制君主,但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以及其他一切大大小小的共产专制君主们,在他们用暴力夺取了政权、又用暴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只从权力政治出发,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的种种作为,已不知给他们的国家、民族和人民带去了多少的灾难,造就了怎样贫穷的局面。相反,被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判了死刑的“资本主义制度” —— 实际上的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和自由主义生产经营方式,却在其后的百余年间,不仅获得了蓬蓬勃勃的发展,而且已在日益地改变着我们这个世界贫穷和落后的面貌,更为解决被马克思所断定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不可调和的矛盾”,即解决“劳资冲突”,逐渐地打开了历史的新局面。
三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认识的错误及其性质
显然,马克思因混淆了两个重大理论问题的界限,才导致他把“资本主义”这个完全不恰当的概念,既当作经济形态的概念来加以批判,又当作政治制度的概念来加以反对。从而为消灭自由主义的经济形态和推翻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找到了一个完全错误的根据。
首先,用“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来取代“自由经济”的概念,便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错失。因为资本主义说到底,它的三个基本内容,不过是本钱、投资和利润而已。它的一个基本程式,亦无非是“投资、获利和再投资、再获利”直至循环往复罢了。如果是在无市场风险的情形之下,这一循环往复便可以持续下去,利润可能越赚越多,投资也可能会越来越大;反之,如果是在遭遇市场风险的情形下,出现销售危机,使制造或买进的商品无以销售或造成得不偿本的情形,则利润的减少,本钱的亏损,甚至是借贷能力的丧失,就完全有可能造成投资的减少,直至投资行为的结束,即“拥有本钱进行投资以赚取利润行为”的被迫终止。由是可知,一个有本钱者,就有投资的可能;一个投资者,便有可能赚取利润。而由投资者即资本拥有者的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商品生产和社会商品买卖的现象,不仅被马克思所指责的“资本主义”社会有之,而且自人类有了生产和交换,它就开始了发生和发展。欧洲在中世纪前就有了商品的制造和买卖,即有了投资者;阿拉伯远在公元前就有了制造和买卖商品的繁荣都市,也就是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繁荣景象”;中国在秦始皇以前就有了个体户,明清两代的大商贾更是资本甚巨,令人称羡。若依马克思的理论竟是有了“大资本家”了。因此,如果仅仅把由本钱、投资和利润等自由的,即不希望被权力控制、而只由市场来调节和制约的经济活动,所构成的社会经济行为,当作被马克思所指责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经济行为,甚至是经济罪恶,就无论如何在道理上和情理上都说不通了。
其次,在被马克思所指责的时代和社会,上述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确实得到了空前的自由发展。但这个发展之所以能够空前自由的原因,一是它能够逐渐地冲破专制制度的压迫,挣脱封建权力的枷锁,打破封建商业行会的限制,而逐渐地获得了自由竞争和自由发展的机会和条件。二是因它的发展,而日渐地推动了整个社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巨大变革要求,从而推动了民主革命的爆发和胜利。三是民主革命的爆发和胜利,尤其是政治上自由民主制度的艰难建立,又反转来推动了自由主义经济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这种互动的发展关系,不仅为世界带来了政治上的光明和进步,而且给世界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和昌盛,更因人类基本权利在世界一些进步国家的逐步实现和基本实现,和自由主义经济形态本身的成形和成熟,才又从根本上改变了早期的劳资关系,把马克思所谓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渐渐地推向了能够解决和已经解决的新时代。这才是近代欧洲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政治本质和经济本质。马克思非但没有理解这一本质,而且从一开始就曲解了这一本质,更站到了这一本质的对立面,不仅将“资本主义”这个仅仅作为经济活动的社会经济行为与自由主义的经济形态等量齐观,而且将之与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混为一谈,甚至将它们并而论之为“资本主义制度”,而加以批判和旨在推倒。这就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可笑错误,而且是在实际上对于近、现代欧洲,乃至对于近、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真正反动了。
四 马克思所鼓吹的无产阶级革命及其对象和动力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不仅是认识的体系,而且是行动的根据,亦即斯大林所说的,是“行动的哲学”。也就是说,马克思不仅要在理论上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政治”,而且要在行动上推倒这一崭新的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并将资本的拥有者 —— 资产阶级作为它革命的总对象。只因这个敌人在推翻旧专制制度的历史奋斗中,也曾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力量而活跃在革命的舞台上,因而,在马克思主义者们不能公然否定反对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时,他们就将那一场革命,既定为反封建革命,又定为资产阶级革命,意即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建立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革命。从表面上看,马克思是把“资产阶级革命”看成了一次合法的革命。但他承认它合法的原因,却是要把它更为“合法”地变成下一个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这样,马克思主义就不仅接过了欧洲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革命旗号”,并且利用这一旗号,进一步掀起了一场反对新生民主制度和新型自由经济的“继续革命”。如是,革命一词虽未改变,但革命一词的对象和内容,却已经是天地相殊了。
由是,参加过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既成了“革命”的敌人,而由“资产阶级革命”胜利所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就应该被马克思的“革命”所推翻。此其一。其二,这个革命既有了对象,也就必定要有自己的主体。这个主体,不言而喻,便是正在遭受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工人阶级,即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和剥削者压迫者资产阶级有着“不可调和”矛盾的无产阶级,亦即马克思所说的新兴无产者。
然而,什么才是无产阶级?什么才叫做“新兴无产者”?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无产阶级是十九世纪的一个概念,多少是浪漫化了的,也许是别的什么东西”【注二十三】。罗素既语焉不详,又语焉不确。但他指无产阶级是十九世纪的一个概念,自然没有错。因为无产者之能够成为一个阶级,完全是十七至十九世纪工业发展、即机器化大生产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因为没有由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机器化大生产,也就没有无产阶级这个“阶级队伍”的形成。但是,问题并不在机器化大生产产生了“新阶级”,重要的却是这个“新阶级”形成的“来源”何在。
马克思主义者们回答得很好 —— “是从破产的农村而来”。既如此,倘若我们再要追问一句 —— “从破产的农村里面而来的人,不就是传统的农民及其儿孙们吗?”如果这个问题成立,那我们就可以给十九世纪的无产阶级加上这样一个定义了,即无产阶级乃是因农村破产才脱下了农装、穿上了工装的传统农民。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们所说的新兴无产者。
必须明确的是,一个漫长的旧社会和旧制度的精神传统,是断然不会与这个旧社会和旧制度自身的物质形式同时走进坟墓的。一次革命固然可以推翻一个王朝,但一次革命却绝无可能将与这个王朝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种种传统的思想、文化和观念,同时送进坟墓。因此,从破产的农村里走出来,脱下了农装、又换上了工装的“新兴无产者们”,也就绝不会因为自己刚刚从农民变成了工人,便立即抛弃了传统农民所固有的传统精神甚至习惯,更不会象马克思主义者们所一再宣扬的那样,他们立即便拥有了无产阶级所固有的“优秀阶级品质”。相反,如果套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来说,这些新兴无产者们,因无不打上了传统农民阶级的烙印,因而才与农民有着天然联系;更与传统农民一样,有着对于传统小生产和传统专制制度的天生恋情;和对于逼迫他们破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生仇恨。这大概就是罗素所说的“一个浪漫化概念”的内涵了。
正因为如此,当之还没有穿上工装,即还没有变成新兴无产者的旺岱农民,在听到罗伯斯庇尔为保卫新生的民主政权而砍了国王的脑袋时,便率先暴发了叛乱,高喊着“我们怎能没有国王”的口号,要为国王和王后复仇。实际上是打响了嗣后波庞王朝卷土重来绞杀革命的第一枪。当之已经脱掉了农装、穿上了工装,变成了新兴无产者的俄国农民,不仅已经能够直面逼迫他们破产,并且正在“疯狂地剥削和压迫”他们的俄国资产阶级时,则他们对于俄国宗法制农村的固有恋情和对于俄国新兴“资本主义社会”的天生仇恨,就自然会激发起他们对于“俄国资产阶级及其制度”的一番新仇旧恨。并且,一旦这个新仇旧恨又为他们身上的“共产主义本能”所鼓舞,更被“无产阶级”这个浪漫化的概念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这个更加浪漫化的“革命”,所激发和激荡起来的时候,这个由列宁所发动的,和以俄国破产农民即俄国新兴无产者们为主体的“革命”,其对于俄国二月民主革命及其成果的彻底背叛和公然反扑,也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了。
五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与传统农民革命的历史关系及其现实发展
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只有弄明白了欧洲传统农民与十九世纪欧洲新兴无产者们,犹如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传统农民的“天然联系”,我们才能追寻得到十九世纪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鼓动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传统农民造反的必然联系,即历史关系。才能认识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论是在思想基础、革命纲领、暴力形式还是在等级观念、内讧外斗以及专制复辟的本质上,都与传统农民革命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本相。如导论第一章所述,十九世纪上半期俄国的民粹派们就已经宣称“俄国农民的身上有着天生的共产主义本能”;同时期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者们”,更是直言“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宗法式的小土地所有制”。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不仅严厉地批判了拉萨尔否定农民革命的错误,而且指出:“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巩固联盟才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决定条件。”恩格斯在他的《德法农民问题》一书中,已正式提出了“工农联盟”的原则,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问题”。巴黎公社则在“告法国农民书”中坦白地宣称:“兄弟,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我所要求的,也是你们所希望的;我所争取的解放,也将成为你们的解放……”至于第一国际由对社会主义解释的不同而引起的前期内讧,第二国际由于社会主义的山头林立而引起的无休止内斗,和第三国际开张伊始就已经出现的外相残杀和内相残杀,尤其是三个共产国际对于中世纪罗马国际教廷的刻意模仿和追求,和由苏俄、中共以及当代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因在共产革命的名义之下,为重建专制制度所表现出来的森严等级、无穷内讧、残酷镇压和嗜杀成性,特别是他们对于知识分子的疯狂迫害,及其对思想文化的无穷摧残,早已把传统农民造反的一系列重大历史特征(参见下卷第二章第四节),表现得无比鲜明而又淋漓尽致。同时,愈是在封建落后的农业国家,其传统农民造反革命的历史特征,便在共产革命中表现得愈加疯狂的现实,就更是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与传统农民革命的历史关系,暴露的更加明确和清晰。
无产阶级革命不仅与传统农民革命有着上述历史关系,而且是在近现代对于传统农民革命的一个极端发展。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这个发展,一是革命的对象,由旧的专制制度和专制政体变成了崭新民主制度和民主政体;二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主体力量,由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变成了仅仅由破产农村而来的小知识分子和“新型无产者”;三是传统农业社会要求绝对平等的“永恒空想”,被赋予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美丽包装;四是用共产主义革命的名义推动专制复辟,并实行对于一切反对者、包括对思想文化上之任何歧见者的专政,从而彻底归复了最为黑暗的“教政合一”式专制极权统治;五是阶级斗争不仅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而且更成为夺取了权力的新兴统治集团,在革命的名义下镇压全体人民的“暴力手段”。
注 释
【注十六】 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在美国实行的共产主义新村实验,以彻底失败为告终。
【注十七】 转引自罗素《欧洲哲学史》。
【注十八】 指十九世纪英国激进主义哲学家边沁等。
【注十九】 〔英〕詹姆士·穆勒:《一八三一年的一封信》。
【注二十】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注二十一】 《第一国际成立宣言》。
【注二十二】 《第一国际成立宣言》。
【注二十三】 罗素:《欧洲哲学史》。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