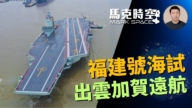【新唐人2012年1月30日讯】【1】
哥已在外地成家立业,在遥远的大城市里生活,属于标准的几年前曾被一再关注的所谓的“凤凰男”。一年365天,哥除了过年回家一趟之外,几乎很难得回老家。今年亦是如此,哥一人回老家过年,而将妻儿留在了大城市。对于“家”,我真的有过困惑的,在许多年以前,我就发出过那样的感慨:
“家,究竟在哪儿?哪一个家才算是母亲的家?是她小时候生活的徐家,是那两间早已沉入历史烟云中的旧草棚吗?还是她与父亲同甘共苦一手创建的二层楼的新家?住多久才算是家呢?十年?二十年?还是百年?以什么标准来评判哪一个才是她真正的家?一个人的家,只能有一个,还是可以有二个,三个,甚至更多个?……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博士毕业后独自一人在比利时的一所大学中工作的哥。现在,在比利时,有他一个人住着的家;在南京,有他与妻子共建的家;在谭家湾村,有他曾一度生活过的父母兄弟住着的老家。这三个家,究竟哪一个才算是他自己真正的家呢?”(见拙作《家是一种感觉》)
许多年过去了,“家”的困惑解决了吗?好像早已经解决了,又好像根本没有解决过。
【2】
那天下午,我带刚回老家过年的哥,去看正在新农村运动中被拆了一半的老家。天阴沉沉的。原本四四方方的院墙,拆得只剩下一座墙门,少了院墙的墙门,显得格外突兀。好在满院子的橘子树,还没有被推土机推掉,仍旧可以闻到往日家的浓烈气息。那是一个梦,一个坚守家的梦。
墙门进去的水泥路上,到处留着鸭子的粪便;三开间的二层楼,被拆掉了一半,只有一间半二层楼和一平顶(厨房)在;最东边那间二层楼,不但不再了,而且连地皮都让挖土机挖掉了,留下一只深深的坑,里面疯长着一人多高的椢树。长时间没人管理的院子的沧桑感,蓦然袭上心头。年久失修的百年老宅,大概有这样的沧桑感的吧。可是,我家的二层楼老屋,只存在短短的不到30年时间啊,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85年)造的啊,为什么这么快就到了命运的终点了呢。
东隔壁阿六家,已经拆完了,推土机的功劳是,上面连一块残砖碎瓦都找不到。阿六的家,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这地球上从来没有过阿六一家似的。听父母讲,房屋拆掉后,上面原本留下许许多多的残砖碎瓦,就像阿六的东隔壁阿多家现在的模样,村里用推土机挖一大的深坑,然后将所有的残砖碎瓦都填进去,上面再覆盖上挖坑挖出的黄土,如此一来,阿六家所在的地方就成了一块平整的黄土地,再也没有什么家的印痕了。
西隔壁阿华家,亦是如此结局。所不同的是,已经成为一平整的黄土地上,被人们种上了油菜,比东隔壁阿六家多了一点绿色。
推开厨房门,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狼藉:各种各样的搬家过后不要的丢弃的杂物,抛洒一地;扑鼻而来的是臭臭的鸡屎味,那是父亲将过年鸡关养在里面的缘故。厨房成了鸡窝,这是1995年建造时,一家人意料得到的吗?谁有这样的本事,能在许多年以前就知道其结局呢?
推开仅存的一扇后门,屋后的景象便展现在眼前。物是人非,物是人非啊。那棵与哥同岁数的大榆树,去哪了呢?那棵曾一再地出现在我散文和小说中的榆树,现在在哪里了呢?
“我不由地想到屋后的那棵老榆树。风,吹得它的枝叶朝一边倒着,倒着,却仍狂乱地摇摆着。那是榆树在作不屈的挣扎吗?那每一片颤抖着的叶,都是它咬紧的牙关在格格发响吗?雨,淋得它像只落汤鸡,从头到脚浑身湿透。那枝叶上不断淌下的雨滴,是拚命抗击风时流出的汗吗?还是受不住无情的摧残流下的乞求的泪?不,这绝不会是泪!榆树,我知道你有一颗坚强无比的心——比我坚强,比我们人类坚强——谁的心会比你更坚强?我们人,自以为人定胜天的人,自以为万物之灵的人,谁能在你面前,拍着胸脯面不改色心不跳问心无愧地说:我比你坚强!如果谁有你一半的坚强——十几年如一日地呆立在一个地方,不移动半步——我将献上我对人类所有的赞颂。这是为什么?三十几年来,我为什么见不到一位像你一样坚强,抱定一个忠旨丝毫不动摇的人呢?老榆树啊,你在追求什么呢?是什么给你如此大的信心,让你在漆黑的风雨之夜仍保持着既有的方向?”(见拙作《窗外的飞蛾》)
有一颗坚强心的老榆树,终于也没能坚守住自己的脚步,也终于消失于无尽的历史之中。就在今年,搬家之后,父母卖掉了那棵榆树,还有河边的那棵老香樟树。两棵树,父母卖了六七千元钱,他们对这价钱很满意。可我,却为之黯然神伤。40年啊,整整40年,才造就了这样一颗大榆树。说卖就卖了,说没就没了。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就一点也不留恋,不觉得可惜吗?
那天放学后,我回老家看望父母,刚到家,就见一辆大卡车,装载着一棵大树,从西隔壁家已拆掉的空地上驶出来。凭第六感的直觉,我知道大事不妙了:我曾一度想保住的老榆树,出事了。果不其然,在屋后见到父亲时,父亲告诉我:刚运出去的,就是那棵榆树。之前,已经将那棵香樟树运走了。
“如果不是这次新农村运动,不将阿华家的房屋拆掉,你要卖这榆树也不可能,即使挖出来了你也没办法运出去。”
父亲淡淡地说。那淡淡的一声,犹如一把尖刀,深深地刺进我的心窝,心猛地一惊,一阵绞痛。我差点晕过去。
西边的夕阳,残红如血。望着脚旁边的老榆树挖走后的深坑,我欲哭无泪。我有一种深深的无助感、无望感、滑稽感。这就是生活么?人们亲手将自己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家园,又一夜之间摧毁了。这是为什么?
我考虑过给父母三四千元钱,将老榆树保留在那,以便将来对村庄有个记忆。可当我想到,自己连老家的房屋都无法保住的时候,我便完全泄气了。“家”都保不住,我还能保住一棵树吗?
“树卖哪儿了?”我机械地问。
“卖到长兴去了,那老板说是搞城市绿化用。”父答。
没啥希望了,这辈子再也看不到我熟悉的老榆树了。再见,我的可爱的老榆树。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但愿树老板能够将你种活!这是我对老榆树最后的一点愿想。
【3】
在农民“被上楼”的新农村运动刚开始时,我有先见之明地给老家拍了照片。整个谭家湾村,我特意角角落落都去走了个遍,拍了个完整的“全村福”。
今天,我领着回老家过年的哥,去看了谭家湾村的现状。这次新农村运动,老家三个村并作了一块儿,在田里重新起造。09年开始的,到今天,三个村两个已消失得差不多了:洋湾村,已完全消失,成了一平整的黄土地,什么印痕也找不到了;北谭家湾村,只剩下桥北的一户人家还没有拆除,其余的都拆光了;我所在的南谭家湾村,细数之下,也只剩下寥寥的六七户人家没拆,整个村破败得犹如刚经历了敌机的轰炸,现状惨不忍睹,与兵荒马乱的战乱年代相似。
这不由得我想起了以前自己写的一篇有关谭家湾村的小文:
“那次去父亲的哥哥——我的伯父——家做客,是在一个阴沉沉的深冬的下午。路上,经过一大片桑树地。桑树全都光秃着枝条,像伸着手臂乞求的老妇。桑地里,不时地有一二个破残的坟堆,偶尔有几只麻雀从身旁飞过,停在桑枝上、坟堆上鸣叫几声。地上的草,早已枯萎,在寒冷的北风中,瑟瑟发抖。整片桑林,呈现出冬的荒凉和破败。
突然,父亲指着不远处的一块桑林说:“你看,那儿就是你爸小时候住的村庄。”我惊谔不已。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一个村庄从大地上消失了,再也看不出它曾存在的任何蛛丝马迹,这可能吗?我想,那儿一定还留有村庄的印记的。可望过去,见到的是与任何一处桑树地相同的桑树地,没有显出丝毫的不同。父亲告诉我:这儿原有一个村庄,村庄的名字叫张家斗。后来,有的人家搬到西边的田湾去了,有的搬到北边的南于家去了,有的搬到东边的塘店去了,如此这搬那搬,好好的一个村庄就没了。搬完了人家,没了人家的村庄,还能算是个村庄吗?残留的破旧房屋,经不起风吹雨打,也相继坍圮了。后来,人们在旧的村庄地上,种上桑树,一年年过去,就长成了现在这样的一片桑树地。
父亲说的是真的吗?村庄也会逝去吗?那么村庄里的人呢?村庄里的猪羊猫狗呢?村庄里的鸡鸣声鸭叫声呢?他们(它们)都到哪去了?一个村庄,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消失呢?什么原因逼着它消失?是因为它离别的村庄——田湾、南于家、塘店等村——太近了吗?村庄与村庄,也像人一样在走着一条竞争之路吗?也像生物一样走着一条适者生存的淘汰之路吗?村庄消失了,对这村庄的记忆也会同时消失吗?父亲会忘记它吗?大地会忘记它吗?流经它身旁的小河会忘记它吗?飞临它头顶在它的树梢上休憩的鸟儿会忘记它吗?谁会记住它?谁又会忘记它?
现在我居住的谭家湾,也会有一天,像张家斗一样从这儿消失吗?连同一村庄人的恩恩怨怨悲欢离合,一村庄的鸡鸣狗吠,一村庄的树木,一村庄的风风雨雨,全都悄无声息地一下子消失殆尽吗?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一天,不知道这一天在何时降临。但我确实知道,这村庄一直在变化着。”(见拙作《谭家湾》)
村庄的消失,说来就来了,真是快啊,快得我还没做好接受她消失的准备。新农村运动啊,你的脚步能不能迈得慢一些,再慢一些呢?!
【4】
农民“被上楼”的新农村运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对此,我曾做过一回总结,给总结出了两点:①新农村运动,其本质是新一轮的圈地运动。②新农村运动,加速村庄的死亡。这种加速死亡,有二层含义:一是村庄的自然消亡、消失。这,也就是我们讲的城市化。农村都变成城市,据说这是大势所趋,是发展方向,不去说它也罢。我在这里,要重点说说的是第二层含义。二是没有变成城市的新农村,村庄亦消亡、消失了。这怎么理解?没有变成城市,不还是农村,不还是村庄吗?问题出在新农村运动的一刀切的完全统一上。
新农村运动中新造的房子,为了好看,为了整齐统一,什么都给高度统一了。我上面已经指出了,这样的房子,是“统一的高低,统一的进深,统一的大小,统一的外表,统一的装饰”的。这样的高度统一的钢筋水泥盖成的房子,一开始还有点新鲜感,觉得好看,觉得美。可仔细观察,看得久了,不引起审美疲劳,那才叫怪呢。
机械的高度统一的新农村钢筋水泥盖成的房子,和小孩子玩的搭积木有什么区别?住在毫无两样,家家户户一模一样的积木一样的房屋中,给人的感觉是住在监狱里。我们的城市建设,已经犯过一次错,将我们全国的城市都建成了一模一样的毫无区别的钢筋水泥积木。现在,在农村,我们又要犯相同的错,将原本丰富多彩,有新有旧,高低错落有致的美丽乡村,搞成和城市一样的兴味索然的钢筋水泥积木。这不是在犯罪,还会是什么?这样的新农村运动,不是对民众的又一次深深伤害么?
搞运动式的建设,可以休矣!否则,我们将无颜面见在九泉之下的列祖列宗!好好的国家,搞成了啥样?善恶皆有报,少作一点孽吧,给农村留下一些村庄,留下一些不一样,留下一些不统一,留下一些不漂亮,留下一些落后,留下一些原始,而千万不要都建成所谓的新农村。有个词叫恶贯满盈,难道他们真的不懂这词的真正意思吗?无语。(见拙作《新农村加速村庄的死亡》)
农民的幸福,就是这样的么?就是“被上楼”?就是欠下一屁股债,住钢筋水泥盖成的积木一样的房屋?就是让村庄死亡?就是终结村庄的命运?
【5】
村庄的消逝,意味着什么呢?有谁思考过这个问题?
“如果这村上出了一位名人,将来要建名人故居,还有可能吗?百年老宅,这样的充满历史沧桑感的词汇,还有机会存在吗?这是在作孽啊!”站在拆除了一半的老家屋后,我无限感慨地对哥说道,“我有一种失去‘家’的感觉,我越来越有找不到‘家’的感觉了。”
“找不到‘家’的感觉”的,又岂止是我一个?
“我越来越觉得如今孩子——尤其大城市孩子,正面临一个危险:失去“家”、“故乡”这些精神地点。
有位朋友,儿子六岁时搬了次家,十岁时又搬了次家,原因很简单,又购置了更大的房子。我问,儿子还记不记得从前的家?带之回去过吗?他主动要求过吗?没有,朋友摇头,他就像住宾馆一样,哪儿都行,既不恋旧,也不喜新……我明白了,在“家”的转移上,孩子无动于衷,感情上没有缠绵,无须仪式和过渡。
想不想从前的小朋友?我问。不想,哪儿都有小朋友,哪儿小朋友都一样。或许儿子眼里,小朋友是种“现象”,一种“配套设施”,一种日光下随你移动的影子,不记名的影子,而不是一个谁、又一个谁……朋友尴尬说。
我无语了。这是没有“发小”的一代,没有老街生活的一代,没有街坊和故园的一代。他们会不停地搬,但不是“搬家”。“搬家”意味着记忆和情感地点的移动,意味着朋友的告别和人群的更换,而他们,只是随父母财富的变化,从一个物理空间转到另一物理空间。城市是个巨大的商品,住宅也是个商品,都是物,只是物,孩子只是骑在这头物上飞来飞去。
我问过一位初中语文老师,她说,现在的作文题很少再涉及“故乡”,因为孩子会茫然,不知所措。
是啊,你能把偌大北京当故乡吗?你能把朝阳、海淀或某个商品房小区当故乡吗?你会发现根本不熟悉它,从未在这个地点发生过深刻的感情和行为,也从未和该地点的人有过重要的精神联系。
是啊,故乡不是一个地址,不是写在信封和邮件上的那种。故乡是一部生活史,一部留有体温、指纹、足迹——由旧物、细节、各种难忘的人和事构成的生活史。”(王开岭:《消逝的“放学路上”》)
是啊,我们正在成为“失去‘家’的感觉”,“找不到‘家’的感觉”,“失去‘家’、‘故乡’这些精神地点”,“没有‘发小’的一代,没有老街生活的一代,没有街坊和故园的一代”!
每一个村庄,曾都是人们的“家”,曾都是人们的“根”。而村庄的消逝,意味着我们将成为无家可归的漂泊的浮萍,意味着我们将成为无根的一代。这是何等的忧伤啊!
【6】
“以前的整个村庄,你都完整地拍下来了吗”哥问。
“都拍下来了。”我答。
“现在这残貌呢?”
“也都拍好了。”
“这就好,这就好!”
我不知道哥说的“好”是啥意思。
村庄的模样,可以被拍下,可以在照片中保存,但“家”能被拍下,能靠照片保存吗?
村庄的模样,可以被拍下,可以在照片中保存,但“家乡”能被拍下,能靠照片保存吗?
村庄的模样,可以被拍下,可以在照片中保存,但“家园”能被拍下,能靠照片保存吗?
我问天,天不语。我问地,地无言。天地间充满了我的天问……
2012-1-26
于笑笑居速朽斋
文章来源:《天涯社区》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