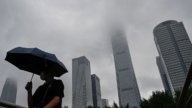伍子胥的父兄,曾死於楚平王之手,他僥倖投奔吳國。日後大舉伐楚,平王已死,伍氏掘墓鞭屍,史稱柏舉之戰。《史記》有言,雖存殺父之仇,但友人認為伍的行為過分了。受此責備的伍子胥自嘆:「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鞭屍與搶屍之間,本來差異較大,但前者的孤例與後者的頻現正在縮短兩者距離。搶屍,這種有悖人倫天理的行為,如今卻被冠以新的稱謂:移除興奮源。這不正是倒行逆施?
自古以來,官民搶屍者罕,更少文字記載。但近年來,此類現象屢見不鮮,蔚為本朝官場傳統。最近一例,就是震驚全國的平度「3·21」縱火案,可為《史記》謀得新篇:
魯人耿福林,世居平度縣。去歲秋,家鄰田畝遇匪,屢現衝突,報警未果,信訪無音,乃輪流守地,攜手進退。是夜四人熟睡,帳外油火併起,一死三傷。族人護屍防搶,至次夜,百警列陣,強搶火化。當日公榜:和諧天下,警維其序。
統計過去十年(2003—2013)進入媒體視線的100起公共事件,其中71件源於非正常命案,57件發生過不同程度的移除興奮源現象。當然,這個樣本缺乏科學性,因為統計口徑的局限,或人為提高了佔比。但是,無論民眾印象,或是官僚體驗,均不否認此舉在實際行權中的濫用。
略舉幾例為證:
——2008年5月,貴州甕安,圍繞女生李樹芬之死,家屬以屍體為挾對抗官府,本無直接利益關聯的民眾加入聲援,後來火燒縣府諸院,成為近年最具標誌意義的群體性事件;
——2009年7月,湖北石首,青年廚師塗遠高非正常死亡,引發數萬人聚集,上萬警力涉入,對抗焦點同樣圍繞逝者的遺體展開;
——2013年7月,湖南臨武,瓜農鄧正加與城管發生衝突死亡,在警方與死者親屬、村民之間,上演了一場遺體爭奪戰;
總體而言,此消彼漲的群體性事件雖以非規範的體制外行為表達,但並不謀求體制內權力的再分配,仍屬於廣義社會運動的初始階段:比如,行動主體多為弱勢群體,肇始於外源性因素——由於他人損害了行動者的利益而引發;往往呈零散、偶髮狀態,仍是區域性或行業性的抗議行動;存在具體、特殊的經濟民生利益訴求,尚在可談判範疇。
「相比甕安,石首事件的處理,是一種倒退。」長期觀察這一現象的中央智庫專家單光鼐說。
甕安事件的拐點意義,在於擁有裝備的警署受到衝擊,這讓金字塔尖感覺底部基石不穩。並且,更多的抗議個體與死者、政府之間「無直接利益衝突」;而石首事件可以理解為政法系統的一次規模反擊,因為這次事件之後,政法委專門製作視頻培訓全國維穩幹部。其中,在群體性事件中強制火化屍體成了標準操作,並美其名曰「移除興奮源」。
這個新詞並非網友的一時起意,已經成為「維穩學」專用名詞。我相信,它是官僚群體與紅色學者基於既有實踐的冷血結晶。
可資佐證的是,四川廣安市委群眾工作局的賀天彬撰文稱:「及時轉移遺體,是縣級人民政府妥善處理非正常死亡事件的關鍵。在非正常死亡事件中,遺體最為敏感,是引發群體性事件的導火索。如果不及時轉移遺體,就無法進入處置秩序,隨時引發群體性事件。要把遺體轉移到殯儀館作為處理非正常死亡事件一道法定程序,確保一旦出現非正常死亡突發事件,遺體能無條件及時轉移到殯儀館。」
這篇至今掛在四川省法制辦官網的文章,在開篇稱,每年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超百萬,2008年廣安市僅安全事故類就有98人,並表示這些措施借鑒了陝西省丹鳳縣等外地經驗。
在群體性事件中,遺體作為死亡的直接表達,或為一種道具,或為一種籌碼,成了官民對壘的重要載體,於是就有了抬屍抗議、善後談判等。用那些當事人的話說:「不怕把事鬧大,就怕成不了新聞。」
從維穩學的角度來看,移除興奮源,首要考慮的不是病理學上的危險,而是社會學上的威脅。移除並善後,就是對興奮源社會危險的一種排除。換言之,強制火化等於將死亡定格為一種純粹的客觀事件,從而控制或消除附加其上的事實細節與情感因素。
因此,搶屍,或曰移除興奮源,就成了一種維穩安排,成了一項規範操作。無論是強制方,還是受制方,可能存在雙重湮滅人性。
但是,尊重遺體,本是人類社會亘古不變的基本底線,即使兩兵交戰,勝者往往允許敵方派員掩埋、祭奠戰友。遺體是否完整,對生人而言是耿耿於懷的一樁心事。孝道中國,遺訓尚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東漢以前,曾設「髡刑」,就是把犯人的頭髮割掉,已是嚴厲的處罰。到後來,就算閹官,早年自宮之物不能丟掉,等到死時合體入葬。
莫怪網友提議,不妨新設一個警種專司「移除興奮源」;這樣的創舉應該申遺,估計韓國棒子不敢來搶。
回到平度縱火案,警方告破案情:受崔連某(承建商)和杜群某(村主任)的指使,2014年3月21日凌晨,5名平度人竄至耿福林居住現場縱火后逃逸,終釀慘案。目前,7人均被刑事拘留。從通報來看,警方此舉還算客觀公正,值得稱讚。但是,接下來的偵查、起訴和審判中,對幾個嫌犯適用什麼罪名,將是地方當局面臨的一大考驗。
長期從事刑事辯護的張慶方律師認為,如果對現場實行犯定了故意殺人罪,承建商、村主任定故意傷害罪,則民眾必然大罵司法不公,袒護權貴;如果均定過失致人死亡罪,當地老百姓還不得造反?如果均定故意殺人罪,不知道承建商、村主任會咬出什麼人?!
這裏派生出一個問題,負責「移除興奮源」的是警方,指令來自於更大的權力方,而背書的對象卻是奪人性命的嫌犯,或是形象崩塌的城管。如此大包大攬,替對方承擔風險,何以收場?我認同張慶方律師的擔心與建議,他說,「無論如何,我還是希望專業人士和媒體能夠公正地引導輿論,不要讓民意再一次綁架司法,從而不合理地加重幾個涉案人的刑事責任。」
民意綁架並在止於善後,還在事前。比如死者家屬的過高要求,以及其他勢力的從中作梗。但話又說回來,誰願意糟踐親人的遺體?「挾屍」抗議之所以盛行,並非行動主體無理取鬧,而是無路可走的弱者武器。試想,連一具不能說話的遺體都害怕,這樣的地方政府何等心虛。
在資訊發達並且強調法治的今天,地方大員一手遮天的絕對狀態已難實現。命案既生,必然要走司法程序。一個健全成熟的司法程序講究證據,並可能展現真相,這又派生了另一問題:在整個司法程序中,雖然行政干預可以影響每個環節,但越往前越有利,尤其是強制銷毀具體的證據(比如遺體)。正如賀天彬文章所述,「要把遺體轉移到殯儀館作為處理非正常死亡事件一道法定程序。」
如此「法定程序」代替或覆蓋司法程序,不能不說令人膽顫心驚。
就目前來看,儘管檢方與法院都可以被影響,但警力成了這種行政干預最有效的工具。當行政、司法沒了制約與監督,淪為合力,更容易把已經完善的司法程序,變成一種掩蓋權力失誤或者罪行的無望循環。
鬥文以計謀,鬥武以警力,鬥法以程序,孰輕孰重,不言自明。只是,當每一條生命意外離開時,不能沒有理由,不能沒有真相。公眾之所以對移除興奮源現象如此憤怒,是因為它突破了天理、人情與國法的底線,讓秩序蕩然無存。
其實,在「壓制」和「退讓」之間,尚存一塊很大的灰色地帶,執政者能夠藉此化解社會抗議帶來的衝擊。如果起初主動拋棄中立調查的身份,強行介入事件甚至主動激化矛盾,那點公信力還能扛得住幾輪消耗?這又何嘗不是日暮途窮?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