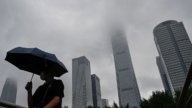【新唐人2011年12月4日訊】紅衛兵是什麼?就是文革衝鋒隊,毛國黨衛軍,極權接班人。這三者集於一身。凡四十五年,基本上,完成了他們的歷史定位和現實核准。其在中國政治中的危害,不自今日始,卻在今天,實現了他們不但不被追究於黨的法則和決議,而且從鄧的金蟬之下脫穎而出,轉變成為中共各級大佬和精英;與毛利用之、再拋棄之之後,登台接班,成為毛鄧二重唱的主角和紅歌今唱的實質主人。雖然,有所謂老三屆「餘孽」跟進伴和,外圍其身,但是,和文革時期「紅外圍」其實不能進入主子圈內一樣,如今之老三屆的醜陋奴僕主義,也頂多是紅衛兵的一個註腳和跟班。這是中國特色政權在文革和今天產生的特殊主、僕關係之一。
一如我們曾經給文革,納粹,社會主義下過不容更改之定義一樣;對於紅衛兵的定義,也無法從這個罪惡的集體名詞中,抽離其醜陋和殘暴的任何內涵。說,某些紅衛兵懺悔,覺悟甚至反水,就要積極肯定云云,那其實是一種另類說法——這個說法就是,這些少數反省派最終列入「反對紅衛兵」的陣營,而非紅衛兵本身有何合理、合法性可言。就像文革裡面那些反對文革者,並不能列入什麼人民文革和大民主之列,只能說,他們是反對者和質疑者——這個提法,最終還會回到如何估價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也不會因為為其加上民主,人民和其他桂冠,就等同於民主納粹和人民納粹;這樣的事情並未發生,也永遠不會發生。納粹陣營裡面那些刺殺希特勒者,不是「人民納粹」,而是反納粹。這是明確無誤的事實。「社會主義」這個列寧毛主義載體,從來也不會因為它被冠以任何光榮定詞而有絲毫改變(世界上沒有民主社會主義—— 北歐是民主資本主義)。
我們說過,紅衛兵,究其實質,其實,就是一種血統和種姓裂變;這種變化,被毛文革時期一時間的所謂戰略錯位所誤導。這個誤導就是,毛要借紅衛兵打擊社會、黨政、國務系統,讓文革極左派控制局面;所以,他施行兩種策略:一是,他支持中學(北京)紅衛兵,打亂社會秩序,造成天下大亂,從中混水摸魚;第二,當中央文革小組實際為其掌控全局以後,他不惜拋棄紅衛兵核心組織「聯動」(北京中學「貴族」紅衛兵),轉位支持反對聯動的中學大學紅衛兵,以打擊聯動之父系官僚體制;最後,這個動向完結以後,他再拋棄大學造反派……直到七十年代末葉,等他死後,由鄧、陳完成他的血統接班人政策。於是,一切饒了一個圈子,最終,從所謂「體制外」接軌於內,促成了聯動接班。這是紅衛兵運動的真正邏輯和真正現實。忽視這個現實,就是為今天的權貴集團中過去之聯動之張三李四變相辯護和吹喇叭。這是新的一種醜陋(接之我們以前批判之「醜陋的老三屆」。)
抓、放聯動的遊戲,早有筆錄於一些作者。摘錄一段如下——
「1967年4月下旬的一個夜晚,近百名『聯動』分子從北京公安局的看守所裡被集中送往人民大會堂。這些『少年政治犯』在這座國家元首迎接、宴請、會見外賓的豪廈中受到國家總理和中央文革主要成員的接見。江青流著眼淚說:『你們受委屈了』。
周恩來說,抓『聯動』是不教而誅,他也動情地流下了眼淚。『聯動』分子身心震顫,痛心疾首。他們相互噓籲、熱淚漣漣。
「他們被宣佈當場釋放。聯動分子自然是感恩戴德,在三呼萬歲之後,昂然跨出人民大會堂的門檻。隨後,北京各城區的公安分局也將各種類型的親『聯動』分子統統釋放。
消息傳來,京城百姓目瞪口呆。這個玩笑實在開得太大了——當時的中國人還不太習慣於那種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政治遊戲。人們只是在古代章回小說中看到過忽而滿門下獄,忽而雞犬升天的情景。釋放聯動還有一個潛在的原因。聯動分子的大多數都是一年前"八一八"在天安門城樓上受到過毛澤東接見的紅衛兵,尤其是清華附中紅衛兵,是他們最先喊出了"造反有理"的口號,並使之成為『文革』中喊得最響叫得最廣的綱領性口號。時間剛剛過去不到一年的時間,昨日革命小將,今日反動分子,於情於理都講不過去。從『文革』的長遠利益出發,紅衛兵運動是不會因此而被否定的。周恩來在接見時,特別追問清華附中紅衛兵來了沒有。紅衛兵創始人1986年曾撰文敘述過當時的場景(見清華附中紅衛兵創始人卜大華的回憶文章,1986年第十期《中國青年》雜誌)。
「在人民大會堂,由黨和國家最高層領導人接見政治上『持不同政見』的學生的事情,在『文革』的歷史上發生過兩次。
「聯動的被接見是第一次。『聯動』的政治生命雖由此而告結束,但是就其成員的命運而言,並沒有因此影響到他們今後的前程,無論是在『文革』中,還是在『四人幫』倒台之後,確屬惡始善終。
「第二次接見是在1968年夏天。由於毛澤東派遣的『宣隊』被清華大學的造反派用武力阻擋在校園之外。毛澤東親率林彪、周恩來及中央文革的領導成員,在人民大會堂接見蒯大富等五大學生領袖。偉大領袖指責造反精英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五大領袖』的政治地位隨之一落千丈。『四人幫』倒台後,幾乎都被投入監獄,惡始惡終、身敗名裂。」(資料)
這便是中央關於文革《決議》絕口不提紅衛兵問題的秘宗和癥結,並為一般文革史料和文革定性研討者有意無意忽視和規避之。這個秘密的要害,就是紅衛兵接班。對於毛而言,造反派是文革的最大功臣;對於鄧而言,紅衛兵是接班的最好人選(他給造反派以致命打擊,稱其為要打擊的「三種人」……)——這二者合二而一
——其中的要害是,鄧要任用血統世襲政制;他當然要迫害毛利用民粹主義時期的造反派,大學生;雖然,在此一點上,毛給人一種「人民」領袖的假相;而鄧直接搬倒這個假相,施行他的紅色「貴族」政治。這兩點的合一是,鄧繼承毛的權力和建制基礎;而反對毛的「打擊」紅衛兵政治(而毛釋放聯動於當年,業已為他們後來接班做出讓步)。故此,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更多的統合,對於他們則是,要在不同形式的共產黨統治下,施行變通的文革策略,反文革策略和駁斥與贊同毛主義策略。也就是我們提到的,權力基礎和利益基礎在文革前後的協調一致。這是他們出台「決議」和「改革」的首要前提。一些人幻想鄧時期可以搬倒毛的權力旗幟。殊不知,鄧砍旗之舉動等於自殘。他根本不會動搖這個權力基礎。因為鄧以後錢財的基礎來源就是毛奠定的權力基礎和世襲基礎。
我們屢次提出這個課題,卻並未引起坊間文革研討者的注意。現在,源於這個課題的缺位和疏忽,很多似是而非的觀點趁機而入。我們看到,文革研究出現的另外一種為紅衛兵辯解的軌跡正在蔓延囂張。這種嘶喊,主要表現在,為文革時期的紅衛兵打死人辯解(卞仲芸案件被她們說成是「挽救」之……);為文革肇始者(歷史的禍害之首)清華附中元創紅衛兵辯解,謂其不主張武鬥——這就好像戈培爾為自己辯解,他自己不曾掏出手槍……為整個紅衛兵全國造反、屠戮和鎮壓(協助黨國)辯解,謂其造反有理,民主有功;為林彪及子辯護,說他們是荊苛刺秦(殊不知那些刺事都是康生和周偽造的事實)……為毛主義歪曲的巴黎公社和「不斷革命」叫好,卻不知毛根本就不施行點滴巴黎公社原則——而此公社原則,大違西方政治路徑和普世價值,早就為雨果,左拉等人痛擊之,揭露之……這種辯解甚至謂張春橋為理想主義,江青為女權主義,毛為民主試驗、試錯主義。最後,他們轉了一個圈子,告訴國人,紅衛兵還是有積極作用於歷史,於現實的;因為,他們後來轉變成為什麼另類東西了。
這就是我們說的紅外圍主義核心。為此紅衛兵辯護者也說了他們出身的「二」類性質——也就是我們所謂中國特色民主黨派之二類性質(「二」,是北京話指責那些雌雄共體之閹人一類者)——這個紅外圍的歷史,亦不自今日始。我們所謂「四四派」(北京中學文革時期之保護黨委、軍隊之一派),就是這類團體。這類團體的特徵,就是在絲毫不觸及和不能維護自身利益的古怪情勢下,為主子和紅衛兵辯護;這個辯護主要體現在,後來他們和卞仲芸「拯救者」(宋彬彬等人)沆瀣一氣,製造偽史,顛倒黑白,胡說八道。這類人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反省者和覺悟者,而是不折不扣的混淆是非,混亂史料者。他們現在似乎佔據了文革研究的主要位置,且在各種邊緣性報章上,以訛傳訛,禍亂文壇。那些被這些人震撼者不知內情,還在為此顛三倒四的假懺悔叫喊叫好,真是可發一笑。
進而論之,四三,四四派的特徵是什麼?倚靠子虛烏有的「不斷革命論」和「公社原則」起家的四三派,既是過時黃花,四四派又是如何一種思潮?其緣起的大致情形又是如何?我們說,這是毛極權主義思想國有化和洗腦運動的兩顆毒果。四三派是毛和托洛茨基極端革命叫囂的產物,他們產生毛之第一種意志;這個意志用來造反和革命——獨仗此意志,不能實行專制極權統治,相反,他每日每時產生所謂的反抗,毛也每日每時堤防之,撲滅之;這樣,毛即便在最極端使用這個意志的時候,也必須轉向第二意志——就是前述體制內壓制、控制和分化。所以,四四派的基礎,其實,比較而言,相對於四三派更加牢靠;這當然是對於統治者和順民奴才附庸而言。表面上,四三派打打殺殺,而四四派修修補補,這是陰陽兩卦的對峙、倚靠和和諧。但是,四四派引發的課題研討尚不止於此。
我們看到,四四派中人,既不是聯動特權分子那一幫,也不是四三派多為知識分子子弟(漢少數幹部/黑幹子弟)那一幫。這個血統的分梳帶來一種「紅外圍」的說法。這是極權主義保守和造反的兩端。沒有這樣兩端,毛的遊戲自然很難展開。對於軍隊的所謂四四式支持,也說明了這一點。大致而言,四四中人有礙於造反的情結。這個情結,當然不是因為(就如聯動一樣)其為十七年的既得利益者,權力的寵兒和無法無天、不受法律約束者,相反,他們中很多人的父母,都是受迫害者——受迫害者起而捍衛迫害者——這就是極權主義政權、社會和人眾的特有典故。這是西方人所說的斯德哥爾摩情結:你越是剝奪和侵犯其人格,尊嚴和利益,他約會覺得你是權威和霸道,從而再三再四地探討這類救世主的魅力,內涵和可塑性。
這個四四派風格業已貫穿整個中國大地。從文革開始,迄今,並未改變。他們這些人很難理解造反者、真正的造反者起而推倒克力司瑪迷信的任何舉動。他們說,一切都會漸變的,只是我們不可以輕舉妄動,以造成社會動盪,成本過大,穩定破壞……他們說,四三派否定毛主席,否定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否定解放軍,真是罪莫大焉——這個說法的今天版本,就是要「救黨」,要否定毛、肯定黨,肯定毛早期,肯定新民主主義,諸如此類。我們說,當極權主義統治喪失了四四派這種附庸,他們就如喪考妣,不可終日——而奴才眾人也會因此大叫,文革聯動之「維護秩序論」和四四派的「捍衛十七年」;……這就是我們所謂四四派心結,四四派「毛」病,四四派奴相。可惜,這樣的四四派人眾,過去是中國大多數,現在仍是。這是我們考察四三、四四的另外一種發現。很可惜,這個發現對於中國更加可悲。因為四三派中人,如果從毛造反,變成真造反,不無可能;四四派中人,變成此類真正異端的可能性,等於0。
阿倫特說,「從理論上說,在極權主義政權下也可選擇做反對派;但是,假如自願的行動只是帶來每一個別人都能以任何方式承受的『懲罰』,這種自由就幾乎是無效的。」老阿的闡述比較晦澀。我們結合中國實際的詮注是,一,極權主義制度下的「反對派」有幾種;主要表現在毛主義、民粹主義造反時期的兩種類型;一種,是革命時期的造反派,解放軍和地下黨;一種,是文革時期的派係爭鬥和造反派、紅衛兵之間的,為了毛主義的廝殺。
二,這樣的反對派,其實是附庸派;一切以崇拜和完成毛主義戰略和策略為轉移。這樣的造反出格,或者不出格,都是毛主義體制內、外權力爭鬥需求的表現。
三,這類「自願」和結社「自由」,莫不是毛毀滅結社自由的變型記和變戲法。這種造反的性質,就是打擊毛旗幟下的他人——造成他人就是地獄的運動類型,而取締真正的自由結社和人權意志——文革時期的文鬥、武鬥、亂鬥,就是這類行為。絲毫與自由,與民主無涉。
四,這種中國人打中國人的自殺式鬥爭,當然以「帶來每一個別人都能以任何方式承受的『懲罰』」為起點和終點。這樣的懲罰,一是,表現在人民反對人民的殘暴鬥爭之下;另一方面,表現在官方對於人們的鎮壓上;前有造反,後有鎮壓。這是文革荒誕殘暴悲劇的始終。
五,如何整體辨正全國的紅衛兵運動和紅衛兵中人,是一個難題。但是,刪繁就簡,我們說,其實,除去全國為毛驅使的一般紅衛兵(四三、四四,天派、地派,團派、四一四派及外地諸如此類的派系,等等),都是毛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烏合之眾和一般打手;含那些思想上的打手和附庸;真正關鍵的紅衛兵實體,就是一,當時的造反派——為毛打擊劉、鄧者;二,後來的紅衛兵接班人(聯動,老兵)。這才是文革的真正辯證法。
於是,真正的紅衛兵定位和詮釋是,他們是文革真正的為害者,領導者和實踐者;他們的出現,只有納粹德國的黨衛軍和衝鋒隊可以類比;不同的是,法西斯覆滅於盟軍的打擊,而紅衛兵,卻在中共崛起的同時完成接班。這是黑白衝突絕對鮮明,迥然大異於之之現實,之悲劇。人類之中,迄今為紅衛兵辯護者中外皆備,不一而足。這些故去,尚存或者人還在心,不死者,仍然千方百計為什麼紅衛兵之中的反省者辯護叫好。是的,歷史的例外是存在的。紅衛兵中人不但反省者確實存在,就是反共者,坐牢者,死亡者,也是存在的;但是,這絲毫不能說明「紅衛兵」這個蓋棺論定的罪惡名詞有任何正面積極意義上的內涵與外延。這是鐵板定定的事實。不要說他們其實並不反省,如宋,如駱,如蒯,如聶……他們不是在為自己辯護,就是在為毛唱讚歌(姑且不提其名姓氏)……與其說,他們是在反省,不如說,他們一直以來,就在反撲。所以,澄清紅衛兵實體和紅衛兵思想,任重道遠。我們這一代,也許不幸於斯,碰到如此眾多為其辯解者和混淆者。那麼,我們的後代如何呢?我們的子弟如何呢?悲觀與之,還是樂觀與之,真不好說呢!
文章來源:《縱覽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