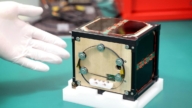【新唐人12月08日訊】作者﹕克里夫‧巴克斯特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以前,我從未想過自己會介入這個“意識研究”(consciousness research)的最前端──“生物通訊”(biocommunication)。回想起來,我所有在教育、訓練、就職方面所作的選擇,還有我天生的好奇心以及許多巧合,似乎都在為這一天和以後的經歷作準備。
我的意識研究生涯並非從植物開始。早在十幾歲時,我就對“催眠”這個主題非常著迷。我當時就讀於紐澤西州新布朗什維克(New Brunswick, New Jersey)的羅格斯預備學校(Rutgers Prep School),這是一所隸屬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的寄宿學校。
某晚,一位坐在餐桌主位的大學生告訴我們他白天上心理學的經過。那堂課的主題是“暗示”,教授試著要示範催眠。他拿了一個長頸檯燈和一張厚紙板,並將紙板挖一個小洞綁在燈上,只露出一個光點。他要求學生中一名志願者將注意力集中在那個光點上,同時作出睡眠的暗示。結果並不成功,學生並未進入任何接近催眠的狀態。最後,教授宣告試驗失敗。
就在當晚,我跟室友說:“我們來試試,看會不會成功。”我們擲銅板決定誰是催眠師,誰是受催眠者。我贏了,所以我當催眠師。房間裏有一個長頸檯燈,我們按照剛才所聽到的依樣畫葫蘆。我用一樣的程序暗示他,說著:“你會睡得愈來愈沉,注意看著光點……”等等。神奇的是,我的室友進入一個我從未再看到過的深度催眠狀態。回想起來,我當時做得真是太漂亮了,因為我很從容地告訴他:“現在,我要你張開眼睛,但你不會醒來。我要你走到走廊的另一頭,申請晚間用燈的許可。”預備學校的學生禁止在晚上十點以後開燈,除非經過許可。於是我的室友在催眠下走過走廊,從值班教授處取得晚間用燈許可。他在晚間用燈的登記表上簽名,接著走回房間。
我要他坐下,然後說:“好,現在把眼睛閉上,繼續仔細聽我的聲音。”過了一會兒,我說:“你現在會醒來。我將倒數五下,當我數到一的時候,你會醒來,而且一點感覺也沒有。”倒數完之後,他張開眼睛說:“看吧,沒用。所謂的催眠根本是胡扯。”當我告訴他我命令他做的事之後,他完全不相信。他甚至對值班教授否認他申請夜間用燈許可。我當時已經體會到這次經驗的重要性,值得繼續研究。
我一生中曾經幾次見識到催眠的力量有多強大,而這是第一次。我很快了解到這個事件背後的意義非常深遠。我在羅格斯大學圖書館中找到幾本有關這方面的書,它們對我造成更深刻的影響,其中包括喬治‧埃司塔布魯克斯(George Estabrooks)與密爾頓‧艾力克森(Milton Erickson)的著作。當時的社會對“催眠”這個課題的興趣尚未爆發開來,相關的著作不多,也沒有太多醫界人士或心理學家針對這個項目發表論述。在羅格斯預校待了一年之後,我轉學到賓州蘭卡斯特市(Lancaster, Pennsylvania)的弗蘭克林與馬歇爾學院(Franklin and Marshall Academy),度過了高中的最後一年。我在那裏繼續我的催眠研究,並受邀為學校的科學研習社示範誘導技巧。
從弗蘭克林與馬歇爾學院畢業之後,我決定在德州大學(Texas University)接受大學教育。那趟從紐約市布朗克區(Bronx, New York)到德州奧斯汀市(Austin, Texas)的旅程相當精采。我用父母給我的火車票錢支付一台“印地安前哨”(Indian Scout)重型機車的頭期款。我很快學會了如何騎機車,就拿著一份詳盡的地圖,騎上這段長而有趣的路程。後來我靠著在校園打工付清了這台機車的餘款。
我原想主修土木工程,但當第一學期快要結束之際,珍珠港事件爆發了,那天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我因而改變主意,轉到德州農工大學(Texas A&M)。在當時的「陸軍儲備軍官訓練計畫」(Army Reserve Officer Training Program)之下,這所學校完全隸屬軍方。我選擇加入“裝
甲部隊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作為一個從紐澤西來的菜鳥,我遇到比別人更多的挑戰。我首先將主修改為農業,後來又改修心理學。
我不但在德州農工大學重新開始我的催眠研究,而且規模更大。透過在校園中的頻繁示範,我的觀眾變得像是被設定過了一樣。我只要跟他們說“我將用手比三下”,每一個人都會立刻沈睡。有三分之一的觀眾會進入某種程度的催眠狀態,其中好幾位還相當深入;我會用那些進入深度催眠的人進行接下來的實驗。沒有任何人反對我所作的催眠活動。
1
事實上,這個活動吸引了好些人,其中也包括我的心理學教授。他在心理學課講到「變動意識狀態」(altered states of consciousness)時讓我在在教室裏進行示範。
我曾示範過幾次“後催眠暗示”(p o s t – h y p n o t i c s u g g e s t i o n s)。有一次,我向一個被深度催眠的人暗示“他醒來之後將不會看到我”,但我事實上一直都在教室裏。我對他說:“你將不會看到我,因為我會離開教室三十分鐘。”這個人醒來之後,問其他在場的人我去了哪裏。我並不抽煙,但我拿起了一根點著的香煙,而他只看到浮在半空中的香煙和我吐出來的煙霧。效果太驚人,使這個已經清醒的人感到非常驚慌,想逃離現場。三十分鐘過後,我重新出現在教室中,然而我從未離開。這種能夠改變人類意識狀態,並讓一個人體驗催眠後負面或正面幻覺的可能性,對我造成非常深遠的影響。
德州農工大學的第一學期結束之後,我休息了一個暑假。一九四二年九月,我決定騎著我的機車從德州大學站(College Station, Texas)出發前往加州,作一趟為期五天的旅行。我沿途走訪了長灘(Long Beach)、杭廷頓海灘(Huntington Beach)、洛杉磯和好萊塢。在那裏我遇到了唐‧賈司林(Don Joslin),他當時於海軍服役,在加州駐防。唐來自一個“神智學”(Theosophy)家庭。“神智學社”(The Theosophical Society)是一個研究、分析並發表從古至今任何宗教及神秘傳統資訊的組織。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東方哲學。唐比我大幾歲,即將被派往海外。我們聊到我的催眠經驗,以及他對神智學教義的認識。這兩天內,我們夜以繼日地交換彼此對於變動意識狀態以及精神信仰的想法。
這些討論讓我了解到,可能有比“暗示”更深奧的概念存在於其他的信仰體系當中。唐‧賈司林引領我初步接觸一些東方思想,例如死後的生命延續以及輪迴等等。不過,一直要到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當我幫植物接上測謊儀之後,我才完全相信,在科學能夠證實的有限範圍之外,有更多的事情正在發生。這個發現使我憶起那些對話。我不知道唐‧賈司林是否平安度過戰爭,但我珍惜兩人的偶遇,因為他帶我進入更深的哲學探索領域。我和他在加州相處的這段時間讓我對進行中的戰爭有更深的體認。我當時快滿十九歲,而且我老家的兵役委員會非常積極地徵兵,使我的正規教育註定無法繼續。
我在德州農工大學註冊了第二個學期,但學期尚未結束就被美國海軍徵召入伍。
在新兵訓練營的三萬人中,有三百人被挑選出來,接受為期九十天的見習軍官訓練,而我是其中之一。不過,我先被送到佛蒙特州(Vermont)的明德學院(Middlebury College)上三個學期的課,並得以繼續主修心理學。這個學校當時被政府接收,為美國海軍V-12計畫的一部分。(待續)
(轉載自博大出版社《植物,也有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