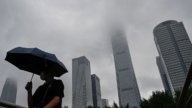我這輩子住的第一間房,在老家什邡最雜亂破舊的老街上,那條街名叫外西街,也叫過建設路,但大家更願意叫它「稀街」,因為它是小城僅有的一條沒有鋪水泥或柏油的街,一下雨便稀泥滿地,難以下腳。
那間14平方米的小房就在外西街172號,我的父親和母親在這裡孕育了我,這裡容納了我從嬰兒到初中畢業的的所有童年和少年經歷。
我對房子和家的記憶,最初始於兩片巴掌那麼大的亮光,那是老屋頂上玻璃明瓦透下的兩小片天空。在它旁邊,是掛著蛛網和灰塵的老瓦片,三者都有些年辰了,一例是古老得讓人喘不過氣來的感覺。
這間只有14平方米的老房子被一道竹篾土牆隔成大小不均的兩小格,外間小些,約佔三分之一,既是客廳也是飯廳還是廚房,這一格上面有木板搭成的小閣樓,堆些平常不太用的雜物,在家裡住房最緊張的那些日子,我曾試圖搭梯子溜上那裡去住,在那裡,我至少可以把四肢向不同方向同時伸開地睡一次覺,但這個計劃後來因為父親想養鴿子賺錢而最終沒有得逞,我們也因此而多吃了無數的灰塵和鴿子身上的微生物。
這小小的房子便是我從出生到初中近10年居住的地方,狹小,擁擠,逼仄,雜亂,而且骯髒。
少年時代,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家裡來客人和買蜂窩煤。這兩件事都會讓雜亂的家變得更加混亂不堪。原本就窄得勉強容得下三四口人的家,會因為客人的到來,而將其中一至兩個擠到門外的街沿上去吃飯,有時客人也會有半個身子坐在門外,拈菜時不得不滑稽地把身子往前傾。而買蜂窩煤的情景更是不堪回憶,在堆滿雜物的桌子下面,泛著臭水的泡菜壇之間有一塊僅能容下一個小孩身子的入口,從那裡鑽進去,就進入到蜘蛛、蟑螂和地蝨婆的世界,這裡充滿了濁惡的潮腥氣,是陽光永遠照不到的地方。
那個僅容小孩進出的小口就是留給我的。每當家裡買煤,我就會鑽進去,由父親把煤從屋外端進來遞給我,由我將它們一個個從地面一直疊到頂攏桌面的位置。每次家裡買一百多個煤,我就會重複一百次這樣的動作,腰酸背痛並吸一肚子的濁氣。我曾經很幼稚地想:幸好我家的房子只裝得下一百個煤,要不可慘了!那樣子很有點像一個窮叫花子在想像皇帝討飯是否會用金碗之類的問題。那可憐的房子,把我的思維也侷限得可笑了。
與外間相比,我更喜歡裡屋一些。這間房子與其說是一間臥室,倒莫如說是一間雜物倉庫。一張雙人床佔去房子的一半空間,另一半,則由一張擺滿箱子、籠屜和各種瓶瓶罐罐的寫字檯佔去。寫字檯和床之間只有很小一個縫隙,一個小孩子可以任意在兩者之間跳躍穿行。這兩個地方,是我人生最早的舞台,我在其間穿越和跳躍出最初的一些動作,而與此相關的記憶,保留至今。
值得慶幸的是,床上還有幾平方尺的空間,這個空間,被蚊帳一包裹,便自成一個世界,一個全封閉的世界,一個看不見外面雜亂紛繁與不安環境的一個安詳世界。雖然被子上終年有一股汗味,枕頭上也有黑黃的油漬,但比之於外面的小房間,我已覺得像是天堂了。
從記事開始,這個世界就牢牢地包裹著我。我至今還能記起二至三歲或更大一點時我的媽媽每天出門時在我枕頭邊放上幾個花生或糖果的情景,那是陪我打發無數個童年時代漫長白天的僅有一點點香甜回憶。除此之外,便是緊鎖的房門裡無邊無際的黑,以及由這些黑反襯得刺眼的那些從木鋪板門縫裡射出的光線。我的許多童年記憶,便是從木板上那一個個小小木疙瘩洞中看到並保留下來的。
被母親鎖在家裡那些漫長的日子裡,我學會了自說自話和胡思亂想。陪伴我半生的自己與自己聊天的習慣,也就是在那個時候養成的。支配我愛好寫作的那些不多的想像力的源頭,大致可以溯源到那張黑暗的床上。
在那裡,蚊帳是蒼穹,竹蓆是大地,疊成堆的被子和枕頭是高低不平的山,枕巾或棉繩是湖泊與河流,火柴盒肥皂盒是汽車或城池,各種方形和圓形的兒童軍棋象棋就是一個個的小兵。
在這個小小的世界中,我是上帝,是王。我指揮著士兵們在戰場上縱橫馳騁;我掌握著山川河流的漲落與枯榮;我想像我的士兵們,像革命電影中那些無畏勇者一樣赴湯蹈火;我被那些固定於意識中的好人最終戰勝壞人的千篇一律的故事結局激動著,快樂著。
這個時候,世界上已經和正在發生著的天翻地覆並影響著我們命運的變化,我卻渾然不知。
這是我記憶中的第一個被稱之為家的地方,嚴格地說,它只是一個不能洗澡不能運動甚至不能讓全家人團圓地坐在一起吃頓飯的箱子,它甚至只能阻擋陽光直射於我們頭上,而對風和雨基本無可奈何。對於它,除了地些自說自話的記憶之外,還有雨天此起彼伏的叮咚滴雨聲,和爸爸媽媽長一聲短一聲的嘆息。
(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