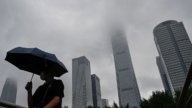【新唐人2012年7月10日訊】一九四七年夏天,時而驕陽似火,時而暴雨如注。二十八歲的羅成基來到了什邡縣。
這時候內戰烽火正在北方土地上燃燒,共產黨的解放戰爭的炮聲已經傳遍全中國。中華民族的歷史正在發生巨大的變革。一個舊政權將要崩潰而尚未崩潰,一個新政權將要誕生而未誕生。然而羅成基卻當上了舊政權的掌權者,做起舊政權「文正公」的好官夢了。
說來也怪,羅成基當縣長,即不是因「剿共」或抗日有功封贈的,也不是靠老婆或姐妹的裙帶從後門弄來的,而真是硬考來的。
早在一九四0年,正在四川省行政幹部訓練團當記錄秘書的羅成基,貿然參加了高等文官檢定考試,竟然得了個第一名。
一九四二年進入蔣介石當校長的中央政治大學,畢業再試時,又居然考了個優等第一名,真是連中二元。
按他的「狀元」資格,鐵椅子和鐵飯碗已拿過手了,按照相關條例,他這個年僅二十二三歲的文官考試「狀元」,可以當上正縣級官員了,然而偏偏出了個「作弊案」。
一九四三年縣長征審時,四川民政廳廳長胡次威等人就勸告他:「你這個娃兒,筆試過關敢保證沒問題,但你必定考不取,你過不了張群的口試關,他對你的筆底功夫有所瞭解,但他用人講究德、智、體、容。你看你那副體容,一副嫩拙拙的娃兒相,你咋個當得了父母官。」
國民黨政學系元老張群,當時是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兼理四川省主席。他親自主持縣長征審的口試。羅成基穩步走進口試場,兩眼自然地掃視了一遍台上的人物,張群坐在中間,陪試官,記錄員分列兩旁。威然的氣氛,岸然的神情。口試開始:
「你對四川的大政有何看法?「張群問。
「目前關鍵是增加生產,改善民生,傾聽民意,鞏固抗戰的大後方。」羅成基從容回答。
「對實現孫總理的建國方略,你對其中四川部分有何設想?」張群步步緊逼。
「發展實業,建設農業,開發交通,振興教育。」不緊不慢,從查清資源,建設水泥廠,到推廣中大二四一九小麥,改良脫籽棉,發展高地灌溉,從厲行禁煙到改善糧政等,說了二十分鐘。言詞裕如。
「如主持一縣之政,你認為應如何恪守官箴?」張群臉上微帶笑容,仍窮追不捨。
「一學包文正公,與民撐腰,為民除害,剛直不阿,執法如山;
「二學范文正公,出將入相,先憂後樂,不貪不賄,身清如水;
「三學曾文正公,春風風人,春雨雨人,戡亂治平,興學育人。」
好個三「文正」,一路的中華傳統貨色,特別是那位殺人如麻人稱曾剃頭的曾國藩,竟然成了他學習的楷模。(當然,近年史學界對曾興文治學剿亂平叛也有所肯 定)這個早兩年學過《資本論》的熱血青年,仍然退回去抱起了封建的衣缽,穿起了儒家的袈裟。「文正」理想,加點「三民主義」,就成了這個中華民國新官吏羅 成基的政治綱領。這些東西怎能醫治苦難深重千瘡百孔的中國?現在看來,真是可悲可嘆。然而,這是歷史。在歷史的道路上,人們啊,你們的足印為什麼會重疊而 交叉,迂迴而曲折,歷史有沒有一條筆直的路可供人們直線前行?
「好!很好!」張群禁不住拍了一下桌子,滿面笑容。口試過關,名列縣長征審第四名。二十四歲的羅成基要當一縣的「父母官」了,要去實現他的「文正」夢了,好不得意。
好事往往多磨,曲終常不奏雅。一個姓陸的入場人落選了。他好不容易找到一條國民政府的法令根據:年滿三十歲的國民才能身任縣長。羅成基作為「縣長年齡作弊案」的首名被告,告到了張群那裡。張群不予理睬。狀子又告到了陪都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吳鐵城處,吳鐵城又把狀子呈送了蔣介石,同時又轉告了張群。羅成基慌了手腳,趕回自貢原籍改戶籍本,又到重慶找考試院的同學幫忙,到頭來還是枉然。面前這個活鮮鮮的羅成基,明明是一個二十出頭的嫩兮兮的小夥子。最後張群只得批示:
「業經考試院覆文……等情,對控告應無庸議。唯縣長系親民之官,學驗俱重,俟年資再長,即予任用可也。」
羅成基這個候補縣長一候候了四年,中間張群意見提前任用,但已離川了。後來經黃炎培、邵明淑、徐勘、向傳義等名高望重的人多次催促,民政廳兩次簽呈,四川省主席鄧錫侯才於一九四七年批准羅成基為什邡縣長。
歷史作弄著人,人作弄著歷史,本來可能走進這一個房間,卻常常走進了另一個房間。也就在這個時候,他的親弟弟羅根基,那個首先從他那裡懂得了點唯物論、辯證法的骨肉同胞,正冒著坐牢的危險,在四川大學從事著共產黨領導的地下進步活動,為推翻國民黨政權發動一次次學潮。而他這個共產黨弟弟的「引路人」,卻在 這個大廈將傾之際去做匡時救弊的「文正」事業了。
二更鑼聲一響,四道城門緊閉。什邡小城便融入了從雍齒時候那世世代代的一片混混沌沌中。除了破嘶的鑼聲伴雜著時斷時續狗吠聲,大街小巷一派死寂。
縣政府辦公廳旁的綠紗窗內,露出疏疏的燈光。今天剛視事的羅縣長正對著一部什邡縣誌在那裡沉思。三更鑼聲響過,突然,從西門外飄進了一陣稀朗的槍聲。他迅疾跑到大堂門口,問正在值夜的衛兵「怎麼回事?」「多半又是西門外土匪搶人了。」衛兵習以為常,似乎聽慣不驚。
第二天下午,四鄉的農民有的背著被蓋卷有的牽著耕牛進了城。大堂門口拴上了一條條水牛。他痛心了,從當夜起,就經常夜間帶隊在城郊巡視堵剿土匪。近郊很快清靜了。但更大的麻煩是西山教匪。人們紛紛傳言:「西山教匪早晚要下山進城。」
西山教匪,就是什邡境內的西山紅燈教。據說十分了不起。他們出發前要燒香唸咒喝符水。出發時一個個身佩黃符紙,手提大砍刀,他們趁鄉下農民逢場趕集之時,場口一陣呼嘯衝進場內。當地團防警察簡直不是他們的對手,一聽「教匪劫場」,往往聞風而逃。聽說教徒們有神靈附體,刀槍不入,如顛似狂,如妖似魔,趕場農民也一聽教匪劫場就丟車棄擔,四散奔逃。滿街店舖也被搶掠一空。前幾年,西山教匪還殺到鄰近的綿竹縣城,殺死了縣官。什、綿兩縣,鬧得人心惶惶。
幾個月時間過去了,紅燈教活動越來越厲害。四川省保安司令部下達命令,對西山教匪徹底剿辦!
羅成基獨坐縣政府中堂,苦苦沉思,有時又起步徘徊,久久不停。情況還不十分清楚,怎麼辦? 這個紅燈教與庚子年間京津的紅燈照有關聯麼?但他們從不反洋教;說他們是替天行道,打富濟貧麼?又從沒聽說他們打掠過土豪劣紳,從不觸犯什、綿間西山內外的馬、宣、趙、蔣四大封建家族的傳統勢力;說他們是政治性的犯上作亂麼?他們雖說殺過綿竹縣官,但純屬對鎮壓的盲目報復,連西山地區的鄉區政權他們都沒提出過反對的口號,更不用說反對國民政府。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啊,是不是鄉鎮勢力與土匪明反暗通,相互勾結,危害百姓?何不借奉命進剿之機,一清除匪患,二翦除鄉鎮惡勢力?不行!西山教徒人多,如果輕率清剿,豈不濫殺無辜,貽害桑梓。棘手啊!怎麼辦?先摸清情況,蒐集證據。
羅成基帶著幾個隨從進山了。從李家碾經高景關至紅白場,當地的鄉鎮長和大土豪馬略三、馬子千聽說縣長駕到,趕緊迎送款待,幾個月來新官上任已燒了幾把火,羅縣長的凶名已響遍四鄉。上任不久就殺了個鄉長,鄉鎮長嘗到了他心狠手快的厲害。聽說他出巡進山,一個個痛陳匪患,堅主剿辦。高橋鄉長還派出民團,扛十支俄制花筒機槍為縣長護行。羅成基納悶了,這些傢伙,對紅燈教怎麼沒有點滴同情的語言?沒有絲毫庇護的馬跡?我是不是錯懷疑了他們?
山色是青青的,水色是澄澄的,風兒是冷冷的。已經是冬月了。羅成基一行人進入一個山溝裡。這裡有幾戶人家,他們還來不及躲藏,羅成基已鑽入一戶人家。一個剛從山上扛木料下山的中年漢子怯生生走了進來,頭上蓄著一個椿芽髦根,身上披著一件沒有毛的棕衣。旁邊一個十二三歲的小男孩露著紅紅的屁股,痴痴地望著這幾個陌生人。火塘前一個看不出實際年齡的女人,穿著一件看不出實際顏色的家機布短衣。裡屋一架床上,鋪著一張破了幾個洞的竹蓆,破洞下露出一團團梭草,頭頂屋樑上,蓋的是一片片杉樹皮。
這一天,羅成基連走了幾條山溝,多數都是如此。他看到,他聽到,這裡的山民吃的都是苞谷糊,好多娃娃沒見過大米。滿山滿谷的林木都不是他們的,但他們照樣要完成徵糧、徵兵、征工,還要隨喊隨到,到鄉長家當義務工,當鎮長家當門戶丁。有的男子到山中扛木放漂摔死,有的小孩到山上打柴被野豬咬死。
第二天,羅成基又私下一人到了馬家溝。這是一個小鄉場。他走進小學堂,學堂內外靜悄悄,沒有人上課。走到街口,一座檯子當街搭,搭檯子的都是課桌。一打聽,原來這裡的老師就是當地的道士,他正為找錢給鄉民開道場。
這天晚上,羅成基臥宿馬鄉長的公館。被縟是暖暖的,心中是冷冷的,輾轉反側,不能成眠,范文正公身在江湖而心憂天下,而我身為一地之長而未憂一境之民。山民飢寒交迫,百姓愚昧無知,土豪泰山壓頂,這不正是「紅燈教」的溫床嗎?平時禍水東流鄰縣,鄉鎮挾以自重,上級一聲剿辦,這不正好是土劣派款購槍,殘殺無辜,勒索山民的良機麼?徹底清剿,豈不是即增長了鄉紳的勢力,又塗炭了苦難的鄉民麼?他翻身起床,撥亮油燈,寫下一首五言律詩,下闕是:
高峰凝白雪,碧霧濕蒼岩。
惺視元黎苦,忡忡忽轉哀。
下山後,他請人書寫來掛在辦公室裡,隨時提醒自己:世上瘡痍,民間疾苦,一枝一葉總關情啊!
一九四八年春天,接省裡命令,成立什邡綿竹清鄉司令部,圍剿西山紅燈教,省裡派了司令,羅成基和綿竹縣長任副司令。綿竹縣買槍練兵,非常熱鬧,正準備進剿,「紅燈教」又出動了,接連掃蕩了綿竹的遵道、土門兩個場。
什邡縣參議會正舉行會議。縣長羅成基坐在行政長官席上,參議員們都到齊了。這些參議員,不少是鄉鎮惡霸勢力的代表。他們望著威嚴的羅縣長,以為今天的施政報告中傳達清剿方略,一定會提出派款購槍的計劃,鄉鎮長們又一次發財施暴的機會到了。羅縣長展開議案紙,一字一句的提出:「實察西山鄉民飢寒困窘,口糧種糧俱缺,民不安生,難以為繼,請准撥積穀六百石以實物發放鄉民,以資賑濟。」會議室一片沉寂。要知道,這些糧谷都控制在鄉鎮的糧倉中啊!
羅成基抬起兇狠的目光,一個人頭一個人頭地盯視,只見一個人頭一個人頭低下去了。好些傢伙都在心中打鼓,肚裡敲鑼:我私挪公糧的事他也許知道了;我吸毒販煙的事他可能抓住點點了……於是,議案一致通過了。
青黃不接之季,羅縣長第二次進山了。他來到三河鄉,把保甲長召集來,命令他們立即到各山各溝,具體查明山民的實際缺糧戶,申報造冊,並通知本人親自來領取。這天上午,三河鄉並不逢場。一清早,四山八野的山民都背筐挑籮趕來了。羅縣長站在一張 條桌上,大聲說:「鄉親們,紅燈教搶人,危害鄉里,必須法辦,但我也看到了,我也聽到了,你們的日子苦啊!你們沒吃的,連種籽都沒有。現在先發一點給你們,暫時維生,以後天下太平了,你們的日子就會好起來的。」然後,又回過頭來對保甲長宣佈:「保甲長私報冒領,軍法從事!」滿臉威風凜凜,簡直像陳州放糧的包文正。就在這個鄉,有近千戶人少則幾十斤,多則百多斤,領到了黃谷。有的老大爺捧起穀子,流著淚說:「我好多年沒見過穀子的樣子了。」
兩次進山,羅成基心中有底了。所謂紅燈教匪,即牽涉到山區百姓飢寒交迫、愚昧無知、受人利用、鋌而走險、徒做犧牲的情況,又涉及到對其他鄉鎮平民百姓橫遭 搶掠,無辜受害的問題。這種出於迷信蠱惑進行經濟搶掠而又並不反對官府及土劣勢力的活動,違背了廣大民眾的利益。紅燈教問題必須解決。怎樣解決?徹底清剿嗎?不行!只能學范文正公西夏撫邊和曾文正公湘鄉辦團的方法,殺其首而撫其眾,才能使民眾免除匪患之苦。
羅成基帶領人馬又第三次進西山了。他已經叫得出大部分山頭的名字,掌握了每條道路的走向。他按圖部署,電話指揮,調兵遣將,分路伏擊,前後兩三個月,時而山前火把,時而山後槍聲,驚險曲折、變幻離奇,演出了好幾幕有聲有色的傳奇故事。然而羅成基雖然可能是個高明的軍事指揮者但畢竟不是軍事指揮者,我這篇東 西可以寫成傳奇故事但不願寫成傳奇故事,所以我就此一筆帶過。紅燈教問題的結局如下:
一、首領王佔鰲、師父楊金洪及其女楊三姑娘,被其夥眾擊斃;
二、紅燈教殘部六十餘人由陳祝安率領請求招安;
三、招安後的紅燈教徒一個不殺,經整訓後發通知遣散回家,令其安居樂土。連綿竹縣押解回來的教匪徒眾,他也一律放掉。
保了山民,除了元兇,清了匪患,頌德之聲四起。省裡嘉獎、什邡慶功,羅縣長似乎應該有「文正公」們戡亂治平的陶醉了。這一天,縣裡各界頭面人物為他設宴演戲。緊鑼密鼓,急管繁弦,一縷縷空虛寂寞渺茫之感不禁襲入心懷。三次進山的情境實施晃動在眼前——民生凋敝如故,土劣猖獗依然,大局已經爛透了。民之不幸,國之不幸,區區幾百石黃谷的發放,小小匪患的平息,是過還是功?是該愧還是該喜?
三年縣長任,殺了多少人?不敢說羅成基是高懸明鏡,明察秋毫,然而,他確實沒殺過一個政治犯,沒抓過一個文化人。相反,他和民主人士公開交往,和革命黨人暗通聲息。
他天天讀報,這偏僻古老的小城也並不閉塞。他讀《中央日報》,讀用《中央日報》做包皮紙所寄的《勝利之聲》等油印小報。徐蚌會戰鏖戰正急,國民黨政權狂瀾 既倒。他走在這似乎平靜的小城內,漫步在縣政府這寧靜的深院裡,望著那憂鬱的天空,今日風雲變幻的中國,哪裡陰?哪裡晴?億萬人腳步紛飛的大道上,該向西?該向東?為這個行將崩潰的政權固守窮城,抱殘守闕麼?他不願!公開舉旗倒戈,棄舊投新麼?他不敢!辭職遠行去香港,去走一條救國救民的新路吧!
一九四八年冬天,他急匆匆來到綿陽專員公署見專員陳瑞林遞交辭呈。陳瑞林是國民黨左派元老熊克武先生的至交親信,又是羅成基前幾年學舊詩的老師和當今的頂頭上司,幾乎成了無話不說的朋友。爐邊酒熱,置腹推心,羅成基提出了辭職的話。陳瑞林說:「成基啊,現在辭職不是時候,我勸你回去好好控制住什邡,伺機行事,錦公(即熊克武)與劉伯承將軍關係很深,未來四川局勢,恐怕還要錦公來收拾啊……。」
心中還沒落實,道路還沒選定,他又從綿陽來到了成都。他找到了國民黨左派要人龍傑三。也是老熟人了,就直話直說吧!江河日下,大局已定,歧路徘徊,怎麼辦?龍傑三先生此時正對蔣介石、王陵基等滿腔火氣:「小弟兄,不必焦,我和賀龍是老朋友了,當年我們一起幹過事。」接著,又悄悄地說:「我介紹你認識一個人。此人是三民主義聯誼會的,我叫他來找你,務必保密!」
一天晚上。有一個人來到羅成基在成都的住所,這人叫程強立。促膝的交談,精心地安排,就在這天晚上,羅成基加入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地下組織。這個國 民黨政權的現任官吏,成了反對國民黨內部反對派的組織成員。他接受了民革組織的秘密指示:抓好武裝力量,控制地方局勢,隨時策應解放軍入川的行動……。
兵荒馬亂之時,冬寒未竟之季,羅成基決定趕回什邡,繼續任職。臨行前一天,他要抓緊完成一件籌算已久的事,急急忙忙來到春熙路。
春熙路上,人流熙攘,這時候,市面上物價飛漲,特別是大米價格一日幾變,金元券如同廢紙,人心惶惶,都在拚命地囤米積物,春熙路邊孫總理的銅像端莊屹立,兩道冷峻的目光,俯視著這不太平的街市。
羅成基走進孫中山銅像旁的書店,這裡卻顯得格外冷清。一打聽書的價錢,不但沒漲,相反還在下降。「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等等。」物質第一看來是個永恆的真理。然而,羅成基似乎反其道而行之,在這飢寒交迫的時節,在舉國上下都在大興「武功」之時,他要搞一番「文治」的事 業了。
八百多年前,歐陽修曾寫過一篇《觀耀亭記》的文章,評述當時什邡文化愚昧,風氣閉塞,不僅老百姓,連讀書人也經常受胥吏差役欺侮的情況。羅成基熟讀此文。三上西山的感受,兩年任內的體察,為什麼邪教歪道在什邡那麼盛行?為什麼一無所有的山民會相信神靈附體?為什麼小學生的課桌成了道士的祭壇?什邡那個悠久的文廟額上那古老的匾額「斯文在茲」和「鬱鬱之文哉」似乎時時在嘲笑著他。什邡貧窮,什邡還愚昧啊!振興教育,倡導文化,迫在實行啊!
從他上任之初起,就立下了幾條不成文的規矩:
一、對鄉鎮長及軍警部屬,他威風凜凜,等級森森,甚至和他說話時只准站著,不准坐著;
二、對軍隊頭目黨務要員特務分子,逢場作戲,嬉笑自如;
三、對文化人士,特別是對學校師生,春風春雨,平起平坐。學生們可以自由進出他的寓所,可以到他的臥室去翻他的書畫。
他到任不久,就到縣中,到師範去提倡學生唱歌、跳舞、演戲;他甚至幾次跑到縣中講課,題目是:《論人才》、《論風度》、《論操守》、《論功夫》……。
不久前,一個發財的機會到了,財政部歸還徵購糧食中的購糧部分的價款二千萬元,這實際上是送給縣中官吏們瓜分的禮品。羅成基心一橫,下令不准任何人挪作他用,全部用來興辦文化教育事業。首先興建縣圖書館。他三天兩頭地跑,現在,什邡縣的第一座圖書館落成了。
此刻,他要在成都為縣圖書館親自選訂圖書。一套民國二十七年出版的《魯迅全集》,一套朱生豪翻譯的《莎士比亞全集》,據說至今還保存在什邡圖書館。就在這一次,他又訂購了三十六套《小學生文庫》,全縣三十六所小學,一所一套。
走出書店,又邁進藝文店,訂購了三十六架風琴。什邡鄉鎮的小學生們沒見過風琴這種「怪物」,也一個小學堂送一架,讓那些鄉下娃娃們學學多來米發梭拉希…………。
「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我們的三年羅縣長,卻喜孜孜換來了一把訂貨單,回什邡後,管他多亂多忙,務必要把三十六部《小學生文庫》和三十六架風琴親自 送到各鄉各鎮的三十六所小學去。雁過留聲,人過留名,這也是給桑梓積功德爭面子興文正的美事。他暗暗打算著,背著西方的殘雲落霞,朝著東天的初月新星,他心兒是甜甜的,腳兒是輕輕的。
小然而,精神畢竟代替不了物質,文治有時是不能和武功相提並論的。「民以食為天」,書籍音樂解決不了老百姓的肚子問題。金元券的下跌和米價的飛漲像兩匹背向 發瘋的野馬越奔越遠,飢餓像千萬條毒蛇威脅著天府之國的人民。一九四九年五月,成都市民鋌而走險,發生了轟動全川的槍米風潮。四川省省主席王陵基下令開槍槍殺飢餓群眾,成都米行前的鮮血正在向全川漫延。
什邡縣政府大堂前,密密麻麻的人群把街扎斷了。這裡有白髮稀微的老太婆,有衣衫襤褸的小姑娘,有坐街守店的手藝人,有走鄉串巷的小商販。平常像散沙一樣的人一下子彙集起三四千。他們一起高喊著:「我們要買米!」「我們要吃飯!」什邡民眾也向縣政府請願了!
羅縣長在大堂辦公室內,雙眉緊鎖,托腮沉思。在他短短的仕途上,大多數時間都是在和糧食打交道。一九四四年,他代表財政部糧食部在川北幾十縣清糧,成百萬石糧沒發生過差錯;一九四六年,他在涪江區做儲運處長,面對胡宗南過境部隊搶米賣高價事件,他揮斥對方的機槍,從容對付了一場危機局面。一九四六年底,他對四川省主席鄧錫侯獻策:「儲其當儲,運其當運,賣其當賣,買其當買」。暫時緩解了成都軍民用糧的燃眉之急……。而此刻,面對著自己治下的飢餓的民眾,該怎麼辦?開倉賣米嗎?縣城的糧倉幾乎空了,杯水車薪,無濟於事。驅趕鎮壓嗎?回什邡,建立了自衛隊,增強了警備隊,這是準備應對緊急的武裝,絕不容許用來對付老百姓。不然,我將成為什邡的千秋罪人。
特委會頭頭進來獻策:「查封商人糧倉,沒收高價米穀。」羅縣長瞥了他一眼,心想,你幾爺子又想趁火打劫。
警察隊長急慌慌進來報告:「請願民眾中可能有土匪混跡其中,乘機鬧事!」
「四周佈崗,加強戒備,便衣抄槍,暗中監視。不准輕舉妄動,沒有我的命令,不管哪個傷人,一律以軍法從事!」羅縣長命令。
大堂外的呼喊聲越來越兇猛.越來越激烈。
羅縣長披上風衣,定了定神,邁著不緊不慢的步子走到大門口,又走上升旗台.街市上的呼喊嘈雜聲沉靜下來.羅縣長往前一站,大聲地說:
「各位父老,各位婆婆,各位兄弟姐妹,米價漲得不成話了,你們沒得吃的,是不是啊?」
「是啊!我們要吃飯!」場子裡回答。
「對!人一頓不吃餓得慌,幾天不吃要餓死人。奸商把米操縱了,你們不答應,我也不答應,我宣佈三句話:
一、 明天早晨起,我保證供應你們平價米。
二、 每個人都帶上門牌(即戶口牌),每天供應。
三、 明天到南華宮買米,只准買我們的,一律不准買商人們高價米。
附帶說一句,如果把門牌借給別人的,改門牌的,是鎮長保長,殺鎮長保長,是平頭百姓,丟縣大牢。散會!回去!」
帶著遲疑的腳步,人潮漸漸地退了。時間已是下午五點了。羅縣長,你的米在哪裡?你是在耍魔法還是在欺民搗鬼?滿縣的公務員都在為你捏汗,特務頭子在等著封倉害人,有米的紳糧在準備轉移埋藏,黨、團、參中有人在等著看笑話。
米在羅縣長心中。
第一個電話掛靈傑鄉,找參議員鄉長宣靜修。這個橫行什邡的通城虎,一聽羅縣長電話,早已出了一身虛汗。
「我是羅縣長,從現在起,你馬上調派召集騾馬雞公車,越多越好,不管你用什麼辦法,必須在明天早晨八點鐘以前,運送三十石大米到城裡南華宮,遲到殺頭。」
第二個電話掛隱峰鄉,找鄉長楊鴻儀。
「我是縣長,你馬上組織騾馬人車,明天早晨八點鐘以前,運二十石米到城裡南華宮,遲到丟你的大監錘你的腳鐐。」
第三個電話!
第四個電話!
第五個電話!……
何等威風,何等霸道,何等無法無天!動輒就要殺人家的頭,丟人家的監。不過,那本來就是個無法無天的世道。為了對付這種無法無天,為了給老百姓吊命,羅成基也無法無天!
三更鑼聲響起,四道城門洞開。城門外的四條大路八九條小路上,「叮咚叮咚」的馬鈴聲、「嘰咕嘰咕」的雞公車聲,響成了一片。隨後,踏踏的馬蹄響,嘎嘎的車 輪響又在什邡城內的三合土路上響起來,驚醒了夜深沉睡的城裡人,他們從門縫向外看,只見一盞盞馬燈,一個個火把向城中心的南華宮流去。天還沒有亮,南華宮的台階院壩裡,都堆滿了白米。
早晨七點鐘,羅成基帶著商會會長、參議會會長、三青團幹事長、縣黨部秘書等來到南華宮,他吩咐這些人去賣米驗門牌。他則站在高高的城樓上,注視著這一切。舒了一口氣,局勢暫時穩住了。
一星期後,什邡城米價降到川西幾十縣的最低水平。
有心解一方之民困,無力挽既倒之狅瀾。在四面八方的米潮衝擊下,什邡的米價也只控制了二十來天。當年范文正公心憂天下,但慶歷新政仍然壽命不長,羅縣長啊,面對什邡蒼生,你個人又有何濟世安危的長策?
一九四九年七月的一天,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王陵基向羅成基發來緊急電令,原來是崇寧民革負責人王蘊滋率部起義了。電令要求:一、立刻率部堵截剿滅王蘊滋的隊伍;二、嚴厲鎮壓什邡去參加王起義的人員,並每日電告情況。
此刻,龍傑三和其他民聯領導人,有的遠去北京,有的正在西康,羅成基和崇寧的王蘊滋在組織上並無聯繫,王陵基電令又泰山壓頂……。怎麼辦?既不能說草率起義響應,以免影響大局;又不能執行命令助紂為虐,只能按兵不動,拖延抗拒。
又一道電令下來了,什邡沒有動靜!
第三道電令下來了,仍然沒有動靜!
最後的電令下來了,什邡縣長羅成基撤職查看。
「羅縣長撤職了!」「羅縣長要回成都查辦了!」人嘴比廣播還快,什邡人都知道了。
垮台縣長羅成基,腳蹬青布鞋,兩袖甩清風,緩緩走出大堂來。身後,是兩年多來的部下隨從;街邊,是什邡的鄉親父老……。
天色是陰陰的,太陽還沒有穿透烏雲,一團團烏雲的四周卻都嵌上了奪目的金邊。走過衙門口,走過留春塢,走過一條古老的大街,街沿兩邊,站滿了送別的什邡人。
從大堂口到腳豬店上汽車,全程五里。這是一種什麼儀式啊?不少人家門口擺著一盆清水,門上懸起一面明鏡。清水、明鏡,還有什麼比這更高的嘉獎呢?羅成基這個三十歲的漢子,竟然流下了眼淚。噼噼啪啪的鞭炮聲中,羅成基用模糊的淚眼,向街邊的父老們頻頻致意。四鄉八方聽說羅縣長要走了,派人送來了幾十匹彩幛。 收下吧?有違自己「文正」清廉的初衷;不收吧?有拂什邡百姓的情義,狠狠心,就收下了。父老們,多謝了!我哪裡是什麼父母官,民眾才是我的父母啊!
汽車開動了。遠處,什邡境內的瑩華山顯出突兀的骨架。路邊,頜水河岸怪石嶙峋,什邡啊!我對你有何功有何德?我哪裡能夠救民眾於水火,解百姓於倒懸?我最後連自身也救不了,我於心何安?我愧對什邡百姓啊!
車出什邡境,羅成基在車上吟成五律一首:
敲擊無窮盡,可憐誦德聲。
瑩山地骨突,頜水石嶙峋。
禹母空陳跡,雍侯祗舊墳。
臨岐一回首,愧疚淚沾襟。
《紅樓夢》中的探春的判詞曰:「才自精明志自高,生於末世運偏消。」我們這位追慕「文正」前輩的才精志高的縣長,在國民政府結束了他的「文正」事業。
青山隱隱,綠水悠悠,在我們這片古老而封閉的大地上,確曾產生過不少憂國憂民,胸懷大志,特立獨行的「文正「之士,他們企圖以儒家的理想改造現實政治,以 個體的清廉療救民生疾苦。他們確乎有一種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的凜然正氣。然而,他們的思想未能突破專制的藩籬,他們的行動未能衝決傳統的羅網。不論他們是以德化人,還是以法治人。他們的個人品質是可敬的,他們的歷史命運往往是可悲的。人支配著歷史,歷史支配著人;人埋葬著歷史,歷史埋葬著人。在歷史的轉折關頭,當社會變革的火山爆發之時,當社會變革的地震來臨之日,火山灰和地震波對被摧毀的對象難免玉石俱焚,甚至多年以後人們把他們從地層中發現,也很難具體辨析這些化石幾分好,幾分劣,幾分假,幾分真……
羅成基,四川省自貢市人。1920年出生在自貢東興寺廻東路42號,鹽業世家。1940年考入四川省行政幹部訓練團,1942年考入中央政治大學。1947年就任什邡縣縣長。1949年辭官回老家自貢。1951年被以反革命罪鎮壓,判刑15年入獄,1962年提前釋放,後勞動改造至1978 年,1986年平反。其後,在自貢第16中學任教,1999年去世。
—摘自張雲初紀實小說《亂世縣長羅成基》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