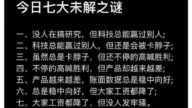【编者按】今年是中共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三十周年。三十年前鄧小平提出并领导实施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得到了很大發展。但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後果,造成中國社會貪汙腐敗猖行;貧富懸殊加大;严重的社会不公,導致民怨沸騰,終於爆發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主運動。时值「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际,我们特开辟「改革開放三十年反思」专栏,将陸續刊登和播放专家学者的有关演讲稿和实况录像,以供大家回顧、反思和討論。
下面刊登和播放的是中國大陸學者劉軍甯博士,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八日在美國西東大學、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和全美中華學人聯誼會聯合舉辦的『中國的歷史教訓和未來挑戰–紀念大躍進五十周年和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國際研討會上的发言:『補天與變天:中國改革的事實與價值』。
【劉軍寧】我是基於這樣的考慮選定這樣一個題目,我覺得在座的,尤其是從國內出來的朋友,起碼是三十年改革的親歷者。我本人是親歷者,又是觀察者。當然有很多朋友還是參與者。我們腦子裡面全部都是史實,我們從任何一個角度都可以講無數的史實。但是對我的挑戰是,我們怎麼樣能夠把改革推的遠一點,然後把改革看得更整體一點,更透一點,然後看到一些我們還沒有看到的,以前沒太注意到的一些方面,有助於我們加深對改革自身,以及中國的認識。
我講的話可能口水比較多,事例比較少,因為我假設大家都知道這些事情,有些判斷我可能舉不出例子,但是大家可能會比我舉出更好的例子,所以我的話不會涉及具體的例子。
我先從紅色中國一九四九年掌握政權到今天二零零八年,這樣四十幾年的一個分期開始說起。從一九四九年到二零零八年,我們可以把它分成大的兩個階段,一個是前改革階段,一個是改革階段。那麼到今天還屬於改革階段,但我們也有人認為中國的改革已經死亡了,但是還沒有人正式宣佈中國的改革已經結束。當然場下的觀眾都宣佈比賽結束了,但裁判和踢球的人還沒有宣佈。
中國三十年的改革可以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一九七八到一九八九年。這個很簡單,一九七八是三中全會,一九八九年是「六四」,待會兒我解釋,我理解的這個分水嶺是什麼意思。
第二個階段是一九八九到二零零二年,為什麼到二零零二年?二零零二年是「十七大」,胡錦濤上臺宣佈說:要搞科學發展;要搞和諧社會。我理解這兩句話的意思是說:鄧小平的改革,鄧小平的發展觀不科學,因爲鄧小皮平的發展觀給中國的社會帶來不和諧,所以胡錦濤要搞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這是對鄧小平的改革路線的一個,說輕一點是調整,說重一點是否定。所以說從二零零二年在官方已經間接宣佈了,鄧小平所幹的這件事,基本上是畫了一個句號,只不過沒有很明朗。
第三個阶段就是從二零零二年到今天,到今天會延申到未來的哪一天,我個人不知道。
改革的第一階段,從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九年,我把這一階段的改革叫做一種「補天」的改革。這是什麼意思呢?從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九年,整個中國人(幾乎很少有例外)有一個共識,就是通過這樣的改革,可以為中國找到一條出路,可以把這個「天」的大的漏洞全部補掉。不需要通過換「天」,中國就會達到一個現代化;就能夠把中國原來所展現的重大危機給它克服掉;中國會平穩的轉向一個新的、美好的社會。這有兩個標緻,一個是一九八四年北大學生打出「小平你好」,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自發的;還有一個不太被注意到的一個證據就是施光南的歌,施光南的歌是一個非常正面,非常向上,非常光明,對未來充滿信心的一個體制內改革派的歌聲,所以到一九八九之後再也沒有施光南這樣的作曲家了,因爲那個時代已經結束了。
作爲「補天」的改革刚出來的時候是有爭論的,而這個「補天論」的代表人物是鄧小平。那麼很顯然,如果要是毛澤東繼續還活著,假如毛澤東一直活到一九七九年,就不會有三中全會這樣的改革。毛澤東肯定認為這個「天」是不需要補的;甚至認為這「洞」還不夠大,天下還不夠亂。毛澤東的看法是「從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毛澤東認為這「天」沒事。另外還有一些人也認為「天」不要補,比如說陳雲。陳雲認為你這個改革,你這個補「洞」,可能是在搗「洞」,是在挖「洞」而已,你不是在補「天」,而是在「天」上搗個窟窿。
還有一些人,比如說像比較有争议的兩個人:一個是林彪,有人說林彪「五七一工程機要」裏面就包含著私有化方案,我沒有仔細研究我不知道。另外一個人就是華國鋒,華國鋒會不會搞改革,我個人也不知道。但我覺得也沒必要深究,既然這個事情是鄧小平幹的,而且是一個不可逆的事件,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功勞,或者是其他的非功勞都積在鄧小平頭上,給這個「補天派」的改革貼上一個鄧小平的標籤。
作為「補天」的改革在中國的出現,是鄧小平發現原來這個舊的「天」雖然還行,雖然換不合適,但是有很多「洞」需要補,所以他決定發動改革來「補天」,這是他的原因。那他的使命是什麼呢?用一句官方的話來說就是:通過改革實現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這是對「補天」的一個很標準的一個解釋。他的方法是什麼呢?方法就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發展經濟這一件事情,作為全黨工作,全國人民工作的重中之重。所以他要做到的一個事,我覺得嚴家祺老師的一個表達很好,不是人民民主專政,而是在共產黨專政下的,有限的、不自由的、扭曲的資本主義。官方的表達法是「有中國特色」,這是一九八九年以前作為「補天」的改革。
那麼一九八九年情況發生了變化,那麼既然這個「天」要補,全國人民就開始群策群力,開始想各種辦法。一個是參與,一個是想辦法來試圖「補」這個「天」。但是有朝一日,這些想通過「補天」的來實現中國變革的人們發現,他們沒有「補天」的權力,他們提出的「補天」的措施被拒絕了,這就是「六四」。
我覺得「六四」的意義(準確地說是「意涵」吧),是告诉我们「補天」是少數人的事情。「補天」,哪些「洞」需要補?哪些「洞」不需要補?那些「洞」怎麼補?那是少數人的事情,不是全中國人的事情,不需要大家的參與。如果大家搶著參與的話,那就會遭到強制地拒絕。而且的確發生了,大家是要搶著參與,大家也遭到了強制的拒絕。那這一結果告訴了我們,以前的這個「天」是補不了的,以前的這個「天」不僅補不了,不僅不可能補好,而且不應該補好,根本就不應該去補。所以從八九年之後,中國出現了一代新人,在座的你們都是。我把它叫做「變天論者」。僅靠改革,僅靠「補天」,已經不足以改變中國的命運了;已經不足以解決中國的問題了,所以出現了這個「變天派」。
那麽這個「變天派」從時間上來說,是一九八九年直接的產物。它包括這樣幾類人,這幾類人在八九年以前很少,只有幾個,他只是一種在監獄狀態的存在。因为只要有這樣的人,他就會到被關到監獄裡去。那麽八九年以前這樣的人大量出現在社會上,包括這樣的幾類人,我把它做一些區分:異議份子、反對派。異議份子是跟政府,跟統治者持不同立場、不同意見的人,他可以是比政府更正統,也可以是對政府更澈底的否定。還有一個是反對派,我把反對派和異議份子稍做一點區別。反對派,特別是在中國的反對派,它是希望通過一種民主手段取得國家權力的人,或者是參與、執掌政府的人,我把有這樣一種抱負的人,稱做反對派。因為中國有很多人是異議份子,有很多人是反對派,這兩個之間有這種區別。
還有出現大量的維權人士;然後還有一個新的的社會階層。還有更多數的人是冷默的人,我不關心是改革是「補天」,還是「變天」。那麼在八九年以前,大多數人認為自己是「補天派」,到八九年以後,一些人認為自己要「補天」了,大多數人認為「補天」還是「變天」跟自己沒有關係。我想直到今天可能還有很多人是這樣認為。
我想講講改革的事實與價值。這句話聽起來好像有點彆扭,我想探討一下,中國的改革基於一種什麼樣的觀念?觀念的出發點是什麼?
我發現中國的改革是基於一種共產黨叫做「唯物主義」的這樣一種觀點,就是物質決定一切。只要我們能夠造就一個物質的事實,這個事情就會發生變化,而觀念是不重要的。所以改革是基於一個「製造事實」的這樣一種出發點,而不是「改造觀念」的這樣一種出發點。
但是我個人發現,所謂「天」嘛,政權嘛,政權是有體制之稱的;而體制背後是有觀念的。所以中國的改革,它把觀念問題忽略了,它變成了一個簡單的製造事實的問題了。比如說很簡單,追求GDP。我們不要說中國觀念發生了哪些變革,政府的任務不是去改變觀念,而去告訴社會,告訴你的上級,你今天的GDP的數字是多少。你的任務就是製造事實,不要去想更多的。不論是鄧小平,還有中國的「自由派」都講得很清楚。鄧小平說:不爭論,不要去爭論姓「社」,姓「資」。因為這是涉及到價值問題。中國的「自由派」說:不要去考慮主義問題,這從胡適就開始了。他們繼承了胡適的口號:「多談問題少談主義」。但是這句話我覺得稍微有點問題,因為你沒有主義就沒有問題,因爲任何問題都是根據一個主義來判斷才促成的。一個狗牠什麼問題都沒有,因為它根本就沒有主義。所以任何問題都是基於主義產生的,當你把主義刪掉的時候,一個社會不會有任何問題。
實際上這一點,改革對價值的忽略,在八九年就體現出來了。當時流行一句話到今天還在說,(我不知道我說的準確不準確),叫「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端起碗吃肉這是一個什麼意思呢?你政府製造的事實很成功,老百姓有肉吃了,端起碗,拿起筷子可以吃到肉啦!這個事以已經到位了,可是到位了以後會發生什麼呢?接著就要罵娘了。這句話本身就講明,改革僅僅單靠製造事實,這一點已經不夠了。
那麼最新的例子就是「三一四」。我沒去過西藏,但是認識很多喜歡西藏的人,從跟他們交談中我有這樣一個發現:從一九七八年改革以來,中央政府拿著大量的錢去支援西藏,基本上是不計成本、不計代價、不計數額,要多少給多少,那麽西藏也有了很大的變化。可是西藏這些人為什麼還在要求他們的那些東西?這說明什麼?說明僅僅靠GDP的數字,不足以替代人們對價值、對信仰的追求。而改革的假設是:只要我給你一個數字了,只要你的GDP得到了一個水準,達到了什麼水準,你的飯碗裏的構成發生了什麼變化,價值問題就消減了。那麽今天足以證明,改革所製造的事實,不足以消減價值問題。
而且改革還有一個很特殊的功能,這個功能以前被忽略了。那就是改革它瓦解了舊的體制的價值基礎。它實質上是瓦解了。你要到中國今天去問,對舊制度,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有沒有信仰者,我想不會有幾個人告訴你他是真正的信仰者。他甚至可以公開的告訴你,他不信仰,或者不怎麼關心。所以改革的發起者意料之外地消減了舊的體制的價值基礎,但是改革自身卻沒有價值基礎,這就是改革的問題。改革以製造事實為使命,它自身卻沒有價值基礎,當它製造了事實以後發現,問題不僅還在,有時候甚至还更加嚴重。
改革的歸宿是什麼?改革會有什麽樣的結局?
我個人判斷,在中國改革是肯定要改的,但最終改革肯定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使命;是一個不可能有結局的,不可能達到目地的這樣一場社會變革。原因很簡單,就像「變天派」所主張的,這個「天」是不可補的,也許在上面打的補定太重,它會把「天」拉下來,所以你補也沒有用,不補你也沒有用。其實中國民間社會在改革一開始就發現了。中國有句流行的話叫做,「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這句話估計流行了十到十五年以上了吧。像當時民間社會認為不需要認何科學論證,不需要讀什麼學位,就判斷出改革不會有一個,像改革發動者那樣所期望產生的理想結局。但是我覺得我今天我對這句話的認識,稍微有一點點深化,這深化在什麼地方呢?你要等死,你不一定死的慢;你要找死,你不一定死的快。因為一開始這句話給人的印象好像是,哎呀,你是等死,你可能會慢一點;你要找死,你不是死的快一點嗎。結果可能是,等死,不一定會死的很慢;但是找死,也不一定會死的很快,就像很多小孩子玩冒險的一樣。 我們從這句話所反應的民間智慧來說,這兩句話給大家暗示是一樣的。民間只對時間做出挑戰;對於結局沒有挑戰。這個結局是什麼,不需要我再說了吧?。
那麽為什麼說改革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使命?是不會達到預期效果的社會變革?
因為在經驗上我們看不到一個先例,看不到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是由共產黨領導的。同樣我們也看不到一個共產黨國家是由資本主義所領導的。這樣的東西 — 一個牛和虎的雜交物,在世界上不曾存在過。你也許見到過騾子;我們也許見到過獅虎,但是我們沒見到過騾子,或者是牛與虎的混合物,我們沒見到過。我們的經驗告訴我們這東西沒存在過。第二,共產主義的邏輯和市場經濟的邏輯,或資本主義的邏輯,是兩個根本對立的邏輯,它們不可能同時存在。在一方做出妥協之後,也許有一個短暫的蜜月,但是他們不可能長期的白頭偕老。經驗告訴我們,我沒見過這樣白頭偕老的先例。我講的是從目標上來看;從內在邏輯來看,改革是不可能完成的。
從方法上來看,我覺得是,現在的這個改革方法,大家也講過很多,我只用一個,叫做:政治上等死,經濟上一點點放活還不是放得很活。其實中國的經濟跟中國的政治一樣,在很多領域都是受到很嚴重控制的。只是大家好像看到經濟似乎活一點,政治似乎不太活一點。其實我覺得中國的政治和經濟改革是同步的,比如你看中國的方便麵價格、石油價格、任何價格都受到管制。但是政治領域裡面,你也可以找到很多自由,你私下你在飯桌上隨便怎麼說,甚至在博客裏面隨便怎麼說,最多給你刪掉,不會有人追究你,所以我覺得中國的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大概是同步的,不大存在政治改革滯後的問題。至少這個差別不是很大。這是它的第一個特點。
第二個特點,從方法來說,它會造成一個後果,就是它用製造危機的方法來解決危機。它每一個改革都試圖解決一個已存在的社會危機,但是這個方法本身,又帶來了新的危機。因為這方法本身是不澈底的。但是它對支持者來說有一個好處,那就是它可以提供一個誤導的解釋。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中國的腐敗,你要看看中央紀委裡面的決議,它說,中國的腐敗是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造成的,主要是舊社會剝削階級的遺毒,可是這些共產黨人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他們一天資本主義的日子也沒過過,他怎麼會被腐朽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所腐蝕?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這是其一。其二,我們再舉一個例子,比如說,很多人提到兩極分化,共產黨認爲兩極分化狀況是資本主義造成的,是市場經濟造成的。其實我們看到,兩極分化並不是資本主義的典型特徵,而恰恰是政治制度有問題才造成兩極分化和腐敗,而不是市場造成的。那麽當在中國統治者暗示的是資本主義改革造成兩極分化的時候,他贏得了很多很多海內和海外的掌聲,這樣他可以在私下竊笑了。
最後我想談三點,一個談談「補天派」的前景;一個談談「變天派」的前景;當然再談談中國的改革情況。中國「補天派」的前景,就是中國改革的前景,也是改革所要改革的體制的前景。但是在我看來「補天派」,尤其是經過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補天派」他代表的是一個過去了的。但是在日常生活當中,我也跟一些跟我認識的體制內的一些朋友交談,他們私下也很開明。他們認為自己是一個「補天派」,他們不想「變天」。可這個不想「變天」並不代表他們是一個信仰問題。那我問他,你為什麼是「補天派」的呢?你覺得這「天」可補嗎?他說我不考慮這個問題,我考慮的是如果這「天」塌下來了,會砸死多少人。所以從我的情感上來說,雖然這個「天」很塌,但我不希望它塌下來,因為這「天」砸下來會傷人。今天的「補天派」和八十年代初的「補天派」的心態已經完全不一樣了。他不是基於「天」可補否,而是怕被這個「天」砸到,他已經是一個非常被動的「補天派」了。當你問他,如果你要是「補天派」的話,你願不願意為補這個「天」做點什麼?他說,很難,我不想做什麼。他只是一個情感上的「補天派」。
最近北京開始「整黨」了,這些體制內的「補天派」都要參與整黨。你問他們喜歡「整黨」嗎?喜歡聽五個小時的報告嗎?他們肯定不願意。你要說出去玩玩也許還行,你要讓我回家寫「整黨」思想報告,他不願意。所以我覺得今天的「補天派」,同八十年代初的補天派已經發生變化了,雖然他們在人數上還是非常非常多。
那麼「變天派」的前景,我覺得「變天派」代表的是中國的未來。因為他對中國未來的方向有一個正確的判斷,至少他們有一個共識,認這「天」不可補,而且事實證明也是這樣。
那麼在中國今天「變天派」面臨的困境就是,他們有明確的方向、堅定的信念,但是他們卻沒有作為的空間;他們有突破的方向,卻沒有突破的能力,這也是中國目前的僵局所在。不過好在,從我在大陸所感受到的,「變天派」的人數,在以一個非常緩慢的速度在一天一天的增加。也許像嚴老師說的那樣,有一個大事件,他就會多很多;有一個小事件他就會少一點;如果完全沒有事件,大概就完全不考慮這個問題了,所以需要有個事件來開啟大家。
最後我想說一下改革的情景,我覺得改革的中國沒有前景,中國的前景在於改制,而改制的前景就在於回到價值上來,回到改革所迴避的價值上來。謝謝大家。
【編者注】作者簡介:劉軍寧,安徽人,一九六一年出生。一九九三年北京大學政治學博士。曾爲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研究員,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訪問學者,現爲文化部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二零零二年,因被举报在北大演讲中宣扬自由主义,被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开除。劉軍寧被稱爲是中國大陸年輕一代政治學者中的領軍人物,著有《民主、共和、憲政》、《權力現象》和《保守主義》等著作。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新唐人首發 轉載請務必注明出處
(聽打:張國華)